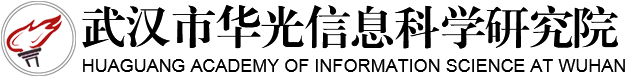本院成果展示
论通信工程的物理范式与传播学的信息范式
论通信工程的物理范式与传播学的信息范式
田爱景1,2,周彩虹3,郭克香1,李宗荣1,2
1 武汉市华光信息科学研究院,中国武汉
2 湖北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中国武汉
3 武汉市汉阳区社会福利院,中国武汉
摘 要:本文作者主张,实现从物理学范式向信息学范式的转变,并不是否定物理学范式的有效性及其适用范围,而是批评物理学范式的“僭越”,即误导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通过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信息化”,可以建立它们自己的学科范式。同为“Communication”的“通信”与“传播”,研究对象分别为“物质”和“信息”,应当遵循不同的科学范式。在实现向信息科学范式的转变之后,我们要致力于探索两种范式的“合作”,让它们一道解释“自然”(如生物基因DNA)、“社会”(文化基因MEME),特别是人类的“思维”。显然,解决柏拉图、笛卡尔以来“身心难题”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关键字:通信,传播,物理学范式,信息学范式,科学范式转变,身心难题
1. 引 言
在香农的论文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里,Communication表示“通信”,他的论文题目被译为《通信的数学理论》。但是,在学术界,Communication又可以表示“传播”,甚至“传播学”。比如,Wilbur Schramm的著作Men, Women, Messages, and Media: Understanding Human Communication,有的译为《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有的译为《传播学概论》。在“传播学之父”威尔伯·施拉姆看来,香农信息模型“提供了一种新的数学理论,该理论既可用于研究电子通讯,也可以用于人类传播”【1,施拉姆,225-227】。他的思维逻辑是:香农信息论是科学,那么运用概率统计和微积分学的数学方法,定量地描述通信过程的客观规律,就是“科学的方法”;这种科学的方法就应当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在“传播学”中不可能是例外。所以,有的学者批评道,施拉姆所代表的“美国主流的传播学派顽固地坚持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和量化研究的路子”;有的学者挑战美国的主流传播学,提出“矫正经验学派的独霸”,“把传播学从施拉姆的钦定体制和书斋里解放出来”【2,何道宽,译者序,pp.4-6】。
2019年,我们曾经与华中科技大学的新闻学院陈少华教授、外国语学院张建伟教授合作,在《社会科学前沿》上发表了题为《通信的数学理论与传播的信息科学》(简称《通信与传播》)的论文【3,李宗荣等论文】。现在读起来,仍然觉得其中的事实、道理与论述没有不当。在准备为国际信息研究学会2023年北京峰会投稿的过程中,我们结合峰会的主题“信息学科的范式转变”进行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在国内外的通信工程学科中,普遍通行的是物理学科的范式,而在传播学中普遍通行的是信息学科的范式,两者“泾渭分明”。在本文中,我们补充《通信与传播》中的论述,呼吁信息科学界与信息哲学界的学者,努力回答信息技术、产品、工程和产业提出的新问题,发挥科学理论与哲学思想的“指导”和“引领”的作用。
2. 通信的数学理论与传播的信息科学,不同的学科范式“泾渭分明”
本文作者在重新研究香农理论和现时的传播学之后认为,在香农《通信的数学理论》的论文中,他运用概率统计和微积分学的数学方法,定量地描述“电信号”在“信道”上传输过程的物理学规律【4,傅祖芸】,完全符合自然科学的范式,被推崇为“定量化”地研究信息的科学模版。但是,香农讨论的“通信”是“电信号”在“信道”上的传输过程,属于物理学的领域;他运用概率统计和微积分学的数学方法,定量地描述的对象,不是“信息”,而是“消息”。香农并没有给出“信息”的确切定义,他认为“信息就是一种消息”。 【5,陈运】消息,作为信息的“载体”,无论是“信号”,还是“符号”,都发生在物理学的“时空”中,都是可以量化的。然而,信息是以“消息”为载体的“内容”或者“含义”;它发生在心理学与文化学“时空”中,因而没有重量、不占据空间;它可以“时间无涉”、甚至“时空倒置”,不可进行时空度量。我们认为:消息,是信息的“载体”; 信息,作为载体的“内容”或者“含义”,它具有演变的过程,但不是“时间”的函数;信息,不是数量化的数学模型和“公式”可以描述;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罗尔斯的《正义论》,操作系统Windows和Android。在这个意义上,所谓香农“信息论”,实为“消息论”。
“消息”,当然是可以“度量”的,而且必须“度量”,否则,电报公司如何计算顾客发出电报的“消息数量”,电话公司如何收取费用?所谓香农“信息”度量的公式,实际上是“消息”度量的公式。这一点,与香农同时代的专家们早就严肃指出了,香农没有反驳。所以,香农从来都不宣称自己提出了“信息论”,创建了关于信息的一般理论;他仅仅说,自己建立的是关于“通信”的“数学理论”。香农深知关于消息的测度、编码以及信道的数学理论,如果被应用到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可能会遇到问题,他明确地警示学者们注意。但是,当时在没有任何“替代的社会公共产品”可以使用的情况下,香农的“提醒”几乎没有效果。
显然,施拉姆误读了香农关于通信的数学理论,误解了香农的“消息论”。他并没有完全理解“消息论”及其使用范围,就认定香农通信的数学理论,既可用于研究电子通讯,也可以用于人类传播,他的出发点和基本思路,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我们认为,传播学研究的对象,不属于物理学、生物学,而是属于心理学、文化学。显然,传播学不是一种香农意义上“牛顿时空观”的“信息论” (即消息论),不属于自然科学,而是属于信息科学。不能削足适履地按照香农的“数学物理方法”的范式,研究“传播学”的概念、原理与方法。我们主张:在信息科学的时空观与科学范式都发展成熟的时候,人们可以重新观察和表述传播学。
在香农论文之前,人类以“语言”为载体,非常成功地构造了数千年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史。从威尔伯·施拉姆开始,传播学的学者们一方面削足适履地宣称,按照香农的“数学物理方法”的范式,研究“传播学”的概念、原理与方法;但是,在实践中却运用了信息科学的时空观和科学范式,重新观察和表述不同于通信工程的传播学。所以说,在事实上,传播学不是一门自然科学学科或者理工科学科,而是一门社会科学学科,它属于信息科学。
3. 与通信工程不同,传播学已经实行了自己的学科范式,但是缺乏学科自觉性
通信工程(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是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属于电子信息类。该专业具有理工融合的特点,以数学、物理和信息论为基础,以电子、光子以及与之相关的元器件、电子系统、信息网络为研究对象。该学科的专业类基础知识必须涵盖电路与电子技术、计算机系统与应用、信号与系统、电磁场与波等知识领域的核心内容,比如通信原理、数字信号处理、通信电路与系统、信息理论基础、信息网络、工程制图学等。
一个通信工程专业的大学生,其基本知识课程方案可以是:数字通信、通信网理论基础、现代交换技术、多媒体通信、无线通信、宽带接入与互联网通信、天线与电波传播、光通信与光网络、移动互联网与终端、射频技术、卫星通信、移动通信等知识领域。具体设计可以是:电路分析基础、模拟电子技术、通信电子电路、数字电子技术、C++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微处理器与接口技术、信号与系统、随机信号分析、数字信号处理、通信原理、电磁场与电磁波、通信网理论基础、现代通信技术。
显然,如上的课程体系,符合“物理科学”的范式,它涉及整个“通信”过程中的相关“物质”的元素,包含物质的系统、技术和工程,以及运用“数量化”和“公式化”的手段进行描述的方式、方法。上述这些,与社会信息及其处理没有关系。
相反,传播学的学科“范式”,与上述的物理学的范式几乎完全不同。它通过汇集各种观点和方法论来研究传播活动,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它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一门科学。简言之,传播学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学科。它具有交叉性、边缘性、综合性等特点。传播学研究的重点和立足点是:人与人之间如何借用传播的作用而建立一定的关系。在国际范围内,传播学研究大体分为两大学派:以美国为中心的经验学派(传统学派)和以西欧为中心的批判学派。
传播专业的主要课程有:中外新闻传播史、传播学概论、新闻学概论、新闻采访与写作、舆论学、文艺美学、基础摄影、影视导论、影视脚本创作、电视节目制作、摄像技术与艺术、电视新闻与纪录片、科教片编导创作、电视节目编辑、媒体动画与制作、网络传播与文化、多媒体应用技术、网络媒体设计、网页设计与制作、广告学通论、广告视觉设计、媒介组织学、传播学研究方法等。
当然,我们注意到:在传播学的相关教学内容中,对于“物理学范式”缺乏防范意识,缺乏传播学“信息”自主的思维模式、观念和理论。在传播学课程中,一开始就宣布认同香农模式的普遍作用,接受香农的信息的定义、计算公式,等等。而关于信息科学,老师则说“信息科学 = 信息论 + 控制论 + 系统科学”。这样传播学要想发展成为一门逻辑自恰、理论自足的科学理论,面临着“先天不足”的困难,需要克服。
4. 信息科学与信息哲学的指导和引领作用
“信息科学”的称谓司空见惯,“信息科学”的著述不断出现。但是,按照物理主义者的观点,迄今为止:“只有信息技术,没有信息科学。”李宗荣邀请美国密苏里大学哲学系系主任J.Bien教授来华访问时,就同他为此发生了激烈的辩论。“结论”来自于评价一个学科是否是科学的“标准”。Bien教授说,科学的标准就是该学科的方法论。因为,除了在通信理论中贯彻香农数学-物理方法之外,其他所有信息学科都没有,都不能算是科学学科。“信息科学”从何而来?
1995年李宗荣回国后,向所在单位申请成立一个“医学信息研究所”。领导批准了,公章雕刻了。但是,物理学教研室一位物理学博士说,可以有“医学研究所”,不应有“医学信息”研究所。医学研究的对象是患病的人体,而“信息”本身,并不存在。请你把“信息”,拿来看看!讲话,是声波;电视,是电磁波;肺部CT的影像,是肺部。如果没有肺部,还有肺部CT吗?
后来,李宗荣到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选听“科学哲学”等相关课程,才知道:信息科学要能够成为一门“科学”,需要关于它的研究对象的哲学“本体论承诺”。信息科学的科学性评价要靠研究信息的“科学哲学家”发言。确立“信息科学”的科学地位,是全部信息科学家的期盼。但是,“信息科学”能不能成为一门“科学”,不是自己说了算。
在进一步地学习中,李宗荣知道了,原来相似的辩论,2000多年以前,就发生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而且以亚里士多德获得胜利而结束。所以,有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物理学之后》(即“形而上学”)流传至今,他的“四因说”也不见衰败。因为,他的观念和人们的“常识”与“常理”相一致。而柏拉图的“理念”是什么,拿来看看!我国有一位著名科学哲学家著书立说:不能在时空中定位的学说,只能是“伪科学”【6,吴国盛】!
直到最近两年,跟着留美博士学到《形而上学》课程的英文版,留德的博士结合古希腊文和英文讲授《古希腊哲学》,李宗荣才大致明白:问题的蹊跷何在。这反映在我们向这次北京峰会“信息社会分会”投稿的两篇文章当中。
李宗荣在理论信息学中定义“信息是信号与符号的含义”;在哲学本体论上,引用柏拉图的说法:“信息”是“非物质的存在”。李宗荣论证了这种东西存在,而且指出它们与“物质”的存在和运动方式刚好相反,比如“信息不守恒”、“无消耗生产”、“同时性共享”等。这些,不能用物理学的定律来解释。然后,李宗荣指出: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是科学的、正确的,但是他在《物理学之后》中的哲学思考,得到“物理主义”观念,是错误的。因为物理主义认为,“物理科学可以涵包世界上的一切,并且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可以最终借助于物理学而得到彻底的解释”。李宗荣说,“彻底”驳倒物理主义,仅仅举出一个“反例”就够了,证明不是一切,不是万事万物。何况全部人文社会现象,都是物理学不能彻底解释的。而没有信息科学的参与,作为自然现象的生物基因DNA的过程和机理,整个自然科学都不能彻底解释。请问:物理学和自然科学的“科学性”需要重新评价吗?
在中国有这样的冤假错案:“亡者归来”。法官说张三杀了李四,判处张三死刑,张三伏法受死,之后李四回家了!张三的家人上访,控诉司法不公平。在讲英语的国家,把“公平”说成是“equity”。在物理世界,有“苹果”才认识苹果的“殊相”和“共相”。人类“生产”了自然界没有的“公平”,于是有了“公平”的殊相和共相。至于“公平”理念如何称谓,如何表达,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可以有自己的选择。显然,“理念”产品是首要的,它的物质载体可以自定、选择、替换与转译。
柏拉图说,在“太阳”的光照之下,我们看到“肉眼所见”之物;而在“善”的理念的光照之下,我们看到“心灵所见”之物,区分好人和坏人,制裁坏人而鼓励好人,推动社会变得更好。“善”是最高的理念,太阳是它的儿子。柏拉图的信息学,是比亚里士多德物理学高出一个层次的学说。这就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根本性区别。物理学本身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正确的、适用的;但是“物理主义”是错误的、片面的、误导的,必须纠正。
5. 结论
本次国际会议的主办者和组织者将会议主题选为“信息学科的范式变化”,是恰当的。我们认为,“物理学”的概念、原理与方法,是合理的、正确的,过去、现在与将来都是如此。我们批评物理主义的片面性,是要明确物理学范式的适用范围和“边界”,指出把物理学的范式运用来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现象,是不恰当的、误导的。因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信息现象,而不是物质现象;人文社会科学必须在信息科学与信息哲学的指导下建立自己的学科范式。
人文社会科学建立自己的学科范式的途径是“学科信息化”,即运用信息科学的范式重新讨论相关学科的研究对象、基本方法、理论预设、概念框架、知识体系,等等。理论信息学的“学科范式”已经被我们成功地应用到心理学、法学、伦理学、语言学、传播学等领域。我们希望,信息科学与信息哲学更好地发挥指导与引领的作用,在实现科学范式转变之后,进一步地推动物理学与信息学两个不同的学科范式“相互合作”,彻底地解释自然、社会和思维中的各种现象。我们认为,笛卡尔的“身心关系”二元论难题,即“延展之物”和“可思之物”在什么地方、如何相处,两者以什么形式、相互作用【7,斯通普夫】,可以是我们即将研究的重点领域。从柏拉图,到笛卡尔,一直没有解决的身心难题(Mind-Body Problem),在实现物理学范式向信息学范式的转变,以及两种科学范式的“融合”中,将得到彻底的解释。
6. 参考文献
【1】威尔伯·施拉姆;威廉·E·波特.传播学概论----《男人、女人、消息和媒体:理解人类沟通》(第二版).何道寛译.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18;第225-227页.
【2】何道宽.译者前言.见:威尔伯·施拉姆;威廉·E·波特.《男人、女人、信息和媒体:理解人类沟通》(第二版);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18;第1-14页.
【3】李宗荣,陈少华,张建伟,田爱景.通信的数学理论和传播的信息科学.社会科学前沿:2019年,第9期,第1698-1706页.
【4】傅祖芸.信息论——基础理论与应用(第四版).电子工业出版社:北京,2018;第1-16页.
【5】陈运.信息论与编码(第二版).电子工业出版社:北京,2012;第1-4页.
【6】吴国胜.什么是科学?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2016;第155页.
【7】塞缪尔·伊诺克·斯通普夫;詹姆斯·费瑟.哲学史:苏格拉底到萨特及其后.第七版.麦格劳-希尔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美国纽约,2003年;第232-2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