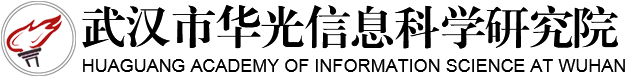友情展示(国内)
华中科技大学博导、何卫平教授成果展示
华中科技大学博导、何卫平教授成果展示
第一部分 简介
 一)个人简历
一)个人简历
何卫平,哲学博士,曾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外国哲学教研室主任。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解释学研究中心暨伽达默尔文献馆”主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第7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全国德国哲学专业委员会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诠释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解释学论丛》主编,《德国哲学》编委,《中国诠释学》编委,《阐释学学刊》编委。曾先后到美国伊利诺依大学(UIUC)、德国海德堡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访学,担任过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客座研究员。曾去美国、德国、希腊、波兰、港澳台多次参加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或交流,并多次主持报告会。研究方向为德国现代哲学,尤专于哲学解释学,涵盖现象学、存在哲学。
主要著作有《理解之理解的向度——西方哲学解释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解释学之维——问题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通向解释学辩证法之途――伽达默尔哲学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学术丛书,2001年)、《高达玛》(伽达默尔)(台湾扬智出版公司,2002年),主编《解释学论丛》(人民出版社);主要译著有海德格尔《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初版,商务印书馆,2016年修订版)、伽达默尔、施特劳斯《伽达默尔与施特劳斯之争》(编译)(人民出版社,2022年)、让·格朗丹:《哲学解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帕特里夏·奥坦伯德·约翰逊:《伽达默尔》(中华书局,2003年初版、2014年再版)。合译、参译的著作有《伽达默尔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解释学、现象学和宗教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西方哲学史》(中华书局,2004年、2009年修订版)等。已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世界哲学》《世界宗教研究》《哲学动态》《国外社会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学术月刊》等重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50多篇,其中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或部分转载有20多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项,参与国家社科重大项目3项,参与教育部主持的马工程重点教材《当代西方哲学思潮评析》(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年)的编写工作。
所著《解释学之维——问题与研究》2013年获第八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12年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关于“Seminar”方式的意义——兼谈德国大学教学中解释学与辩证法的传统》获2011年武汉大学教学论文特等奖。
已为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设过以下课程:《西方哲学史》《西方现代哲学导读》《解释学与辩证法》《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胡塞尔现象学导论》《现象学方法》《海德格尔早期思想》《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哲学解释学导论》《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导读》《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解释学与历史主义》《奥古斯丁的解释学思想》《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导读》《解释学与修辞学》《海德格尔的〈康德书〉导读》《解释学的经验与真理》《狄尔泰<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导读》《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导读》《伽达默尔语言哲学》《伽达默尔与利科的解释学》《笛卡尔与维柯》《休谟<人类理解研究>导读》《列奥·施特劳斯的解释学》《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解释学》《柏拉图<斐莱布篇><蒂迈欧篇>导读》《伽达默尔<柏拉图的辩证伦理学>导读》《利科的文本理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导读》《柏拉图<理想国>导读》《海德格尔的语言哲学》《伽达默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善的理念>导读》《伽达默尔与施特劳斯之争》《柏拉图<美诺篇><斐多篇><会饮篇>导读》《胡塞尔<危机>导读》、《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导读》、《海德格尔的真理观》《康德的历史、政治哲学导读》《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导读》《亚里士多德<范畴篇>、<解释篇>导读》、《康德<判断力批判>导读》等。
已带硕士、博士、博士后共56名。
E-mail:wph_06911@163.com
第二部分 代表作
一)部分代表著作的摘要及目录
理解之理解的向度
——西方哲学解释学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
何卫平
内容提要:
本书着重对以伽达默尔为核心的西方解释学的一些重要的、带根本性的问题作出了深入的研究,它主要由前伽达默尔解释学和伽达默尔解释学两个部分组成,二者具有内在的联系。前一个部分主要分析了“Hermeneutics”的译名以及维柯、德国历史学派、狄尔泰和海德格尔弗莱堡早期的解释学思想,它们构成了理解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前提和背景;后一个部分主要从艺术作品本体论、教化、共通感、判断力、实践哲学、启蒙反思、古今之争、历史主义、辩证神学、修辞学、政治哲学等角度,对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作了进一步地反思和探幽发微。本书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了这个领域的工作。
目 录
自序 1
关于“Hermeneutik”的译名问题 10
人文主义传统与文化哲学——以维柯为基点的两个层面的透视 22
德国历史学派解释学初探——从兰克到德罗伊森 27
西方解释学史转折点上的经典之作——狄尔泰《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述评 55
海德格尔1923年夏季学期讲座的要义及其他 78
伽达默尔的生平及学术道路 96
伽达默尔的艺术作品本体论的解读 108
伽达默尔的教化解释学论纲 128
略论伽达默尔的“Sensus Communis” 145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与康德的判断力 154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中的实践哲学——析此书关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解读及意义 169
伽达默尔与启蒙反思 183
历史意识与解释学循环 203
解释学与古今之争 212
伽达默尔与施特劳斯之争 225
奥古斯丁对西方解释学的影响 247
伽达默尔评布尔特曼“解神话化”的解释学意义 261
从修辞学到解释学 275
走向政治解释学——伽达默尔后期思想中的世界主义眼光 296
关于“Seminar”方式的意义——兼谈德国大学文科教学中解释学与辩证法的传统 308
建构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一种可能的思路——以伽达默尔的思想为参照 324
附录: 330
施莱尔马赫:解释学纲要 330
维特根斯坦:关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畏” 349
二)部分代表论文
哲学解释学的伦理学之维
——析伽达默尔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善”的理念的解读
(《道德与文明》,2019年第6期)
何卫平
【摘要】《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善的理念》是伽达默尔继《真理与方法》之后第二部杰作。它通过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善”的理念的分析,着重阐释了柏拉图在这个问题上的前后关联以及与亚里士多德的一致性,强调二人即便有差异,也不是根本性的,他们一起构成了西方实践哲学传统的伟大开端。伽达默尔这一解释立足于一个新的起点,那就是超越当代德国的新康德派、耶格尔派的立场,包括海德格尔的立场,同时也是在更高层次上回到黑格尔之前的西方传统。它以柏拉图的《斐莱布篇》为重心,上挂下联,揭示了善本身以及以它为中心的实践哲学与本体论的统一。伽达默尔解释学普遍性的追求最终在古代实践哲学中找到了根据,同时它也反映出当代西方解释学的伦理学转型所依靠的重要资源。这部著作的完成,使得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就是实践哲学”著名论断真正落到了实处,解释学的普遍性得到了彻底的实现,在这里,存在哲学与实践哲学、哲学解释学与哲学伦理学达到了统一。
【关键词】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伽达默尔 善的理念 实践智慧 实践哲学 解释学
﹝中途分类号﹞ B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伽达默尔晚年在其“自述”中回忆道:他一生有两个研究重点:一个是解释学;另一个是古代哲学[①]。他生前编纂的《著作集》(10卷本)有三卷是专讲解释学的(1、2、10卷),另有三卷是专讲古代哲学的(5、6、7卷)。与之相关,严格来说,伽达默尔一生大概只写过三本系统专著:《柏拉图的辩证伦理学——对<斐利布篇>的现象学解释》《真理与方法》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善的理念》,其他基本上都是论文或论文集。《柏拉图的辩证伦理学——对<斐利布篇>的现象学解释》(1931年)是他在海德格尔指导下完成的教师资格论文,也是他的第一部专著,这本书可以看作其整个思想的真正开端(而不是他更早的博士论文[②])。沿着这一开端,伽达默尔后来发展出了他的两部最重要的著作:一部是《真理与方法》(1960年);另一部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间善的理念》(1978年)。前者侧重哲学解释学,后者侧重哲学伦理学。表面上看,它们是两个不同方向,但对于伽达默尔来讲只不过类似一枚硬币的两面,二者具有交融性。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间善的理念》(Die Idee des Guten zwischen Plato und Aristoteles)[③]出版于1978年,此书的英译者P.Ch.史密斯(P. Christhopher Smith)将其视为伽达默尔最重要的著作之一[④],西方当代著名伦理学家、伦理学与政治哲学中社群主义运动的代表麦金太尔则称之为继《真理与方法》之后伽达默尔的“第二部经典”[1],类似于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之后的《对哲学的贡献——从“Ereignis”而来》。它体现了《真理与方法》之后,伽
--------------------------
*作者简介:何卫平,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武汉 430074)。
[1]参见伽达默尔《解释学II: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603页以下。
[2]伽达默尔的博士论文《柏拉图对话中的快乐的本质》由新康德主义者那托普和尼·哈特曼指导,他后来非常不满意,一般不怎么提及,他生前编的《著作集》10卷本也没有收入。他只承认他的第一本书是《柏拉图的辩证伦理学——对<斐莱布篇>的现象学解释》。
[3]这个书名中的“Idee”主要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善”的理解和看法,也可以译成“观念”。
[4]参见Gadamer, Idea of the Good in Platonic-Aristotelian Philosoph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vii.
1
达默尔思想的发展与总结[⑤]。可是,以往国内学界对《真理与方法》研究很多,而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善的理念》关注太少[⑥],但实际上后者的意义决不亚于前者,它是伽达默尔整个哲学解释学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现在看来,正如研究海德格尔仅仅停留于他前期的《存在与时间》是不够的,还要进入到他后期的《对哲学的贡献》一样,对伽达默尔的理解仅仅停留于他中期的《真理与方法》也是不够的,还要进入到他晚期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善的理念》,因为只有进入到这部著作,伽达默尔所追求的解释学的普遍性才真正体现出来,并彻底融入到西方实践哲学的伟大传统。
如果说《柏拉图的辩证伦理学》代表他早期的思想,是其思想的真正开端,而《真理与方法》代表他中期的思想,是其哲学解释学的集中体现,那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善的理念》则代表他晚期的思想,是其哲学伦理学的集中体现,也是其思想最成熟的标志。但三者之间有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那就是实践哲学,其基点与核心是伦理学,它通向政治学,是对古希腊以来的传统在现代的一种分有和升华。我认为,这三部著作构成了伽达默尔整个思想体系的骨架,它们之间有交集,有侧重,同时也可以看出伽达默尔思想的总体走向。只有确立了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之后,我们才能更好地去理解其中的每一部,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善的理念》,否则容易陷入“盲人摸象”的片面性中。
我认为,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作为实践哲学突出两个基本点:一个是“实践智慧”;另一个是”善”的理念。二者不可分,前者包含后者,并隶属于后者,它指向一种本体论或存在论(形而上学),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善的理念》从这两个方面,尤其是后一个方面集中展示了伽达默尔解释学的“伦理学之维”[2],其中的内涵、价值和意义非常值得我们深入挖掘。
一、问题意识及背景交待
在这本书的“序言”中[⑦],伽达默尔开宗明义,交待了写作背景,指出他所关注的焦点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统一性,而这个统一性是从效果历史这个角度来阐发的,在这个方面他明显受黑格尔的影响,当然黑格尔更多是从思辨唯心论和辩证法的角度将西方古代这两位最伟大的哲学家联系在一起的[3],但这对伽达默尔无疑是有启发的。他认为,黑格尔之后,二者的统一效果一直遭低估,人们停留在柏拉图是唯心论者,亚里士多德是经验论者这种简单、肤浅的区分上[2](2),而没有看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联系对于当代哲学思考的意义。在伽达默尔大学时代盛行的新康德主义(包括他的老师那托普)在古代哲学中更看重柏拉图,而比较忽视亚里士多德,他们将柏拉图的理念论解读成认识论或知识论,而非本体论,例如,他们把柏拉图的“理念”理解为“法则”或“自然法则”[⑧],以与康德哲学联系起来,这样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理念论的批判就未能得到正确认识,甚至被看作是荒谬的,另外,柏拉图从苏格拉底那里继承来的伦理学论题也遭到了忽视[⑨]。
伽达默尔对柏拉图作为“理念之理念”——“善”的理念的解读不同于20世纪的新康
------------------
[5]关于伽达默尔“第二部重要著作”之前有关基本观点,张能为教授在他的《实践就是伦理学的实践——伽达默尔哲学伦理学的理论构想与意义理解》(载《道德与文明》,2019年,第12期)可以说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读者可参看。
[6]当然对与之关系非常密切的《柏拉图辩证伦理学——对<斐莱布篇>的现象学解释》的关注也不够。
[7]参见Gadamer, Idea of the Good in Platonic-Aristotelian Philosophy, 1986, p.1-6;另参见伽达默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善的理念(序言)》,何卫平译,载《伽达默尔集》,严平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593-597页。
[8]参见纳托尔普《柏拉图的理念学说》(上册),浦林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5页,352页,356页;另参见柏拉图《巴门尼德篇》,陈康译注,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7页(从这本书可以看出,伽达默尔的中国师弟、尼古拉·哈特曼的学生陈康先生的柏拉图研究,就打上了明显的新康德主义的印记)。
[9]柏拉图的对话几乎每篇都包含有伦理学的问题,直接或间接同“好”或“善”(good)相联系,只是他的论述没有止步于伦理学,这也显示出他对苏格拉底的继承与发展。
2
德主义,后者主要朝着认识论或知识论的方向,放弃了苏格拉底的德性论方向[⑩],而伽达默尔重新回到德性论的传统,它通向本体论,并强调亚里士多德并非完全与柏拉图对立,亚里士多德主义乃是柏拉图主义的一个发展方向或“打开”(正如伽达默尔的思想是海德格尔的一种“打开”一样),而这就是伽达默尔的第二部重要著作所要展示的主要内容。
另外,伽达默尔还提到了德国的图宾根学派对柏拉图的研究和耶格尔学派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11],尤其是德国20世纪最富盛名的古典学者之一维尔纳·耶格尔[12]的重要学术成果,即从发生论的角度来探讨亚里士多德所得出的结论,根据他的看法: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为柏拉图主义、中期为过渡期(开始批判柏拉图,确立自己的思想)、晚期则摆脱柏拉图,走向经验主义阶段[2](7)。但伽达默尔对这一说法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他自己这本书的德文名称是“Die Idee des Guten zwischen Plato und Aristoteles”(《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间的善的理念》),其中的“zwischen”强调的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共同的主题和所隶属的传统或遗产,而不是耶格尔所强调的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由隶属到批判、再到走出的发展[4],换言之,伽达默尔这个书名显示出与耶格尔的书名“Aristoteles, Grundlegung einer Geschichte seiner Entwicklung”(《亚里士多德:发展史纲要》)的不同立场:后者强调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的“发展”(Entwicklung),而前者强调二人“之间”(zwischen)的共同所属[2](vii,n2)。为突出这一点,且避免误解,英译本和法译本都用“-”来代替德文标题中的“zwischen”[13],这样译更神似,而且在伽达默尔那里也可以找到根据,其文中本身就有这类表达,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统一效果”[14]。
其实,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思想加以调和的这种研究方式在西方古代和中世纪占优势,例如,将基督教与柏拉图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奥古斯丁也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而在中世纪当经院哲学开始接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时,柏拉图的传统也被完整的保留下来了,例如,迈蒙尼德和托马斯·阿奎那,甚至比他们更早的阿拉伯哲学家阿尔法拉比(公元870-950)的“两圣相契论”就已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15],应当讲,造成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尖锐对立是近代才出现的[5]。
可见,伽达默尔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统一起来理解,与其说是他的创见,不如说是他对黑格尔之前(包括黑格尔)的整个西方传统的恢复,同时从这里也让我们看到,柏拉图主义的历史和柏拉图著作的接受史几个世纪以来的巨大变化,伽达默尔处于这个变化的潮头,审时度势,高屋建瓴,他的这种恢复决不是简单重复过去,而是有着时代要求的新内容的。在这本书中,伽达默尔主要围绕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善”的理念的分析来展示他们之间的共同主题与统一效果的。
另外,伽达默尔这样做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对海德格尔的挑战(当然,可能出于对老师的尊重,他的表达很委婉)。众所周知,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间,海德格尔更看重后者,他把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对存在的遗忘主要归咎于柏拉图,并将柏拉图主义视为形而上学的代名词。而在对待形而上学的态度上,伽达默尔没有显示出极端的反对,而是表现出某种亲和的立场,尤其是晚年,正如让·格朗丹所说的那样,“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可能是20世纪唯一不把自己推介为对形而上学克服的哲学”[16]。这在此书中尤显突出,非常值得后人
-------------------------
[10]参见纳托尔普《柏拉图的理念学说》(上册),浦林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336-349页。
[11] 参见Gadamer, Idea of the Good in Platonic-Aristotelian Philosophy, p.7。另参见拙译,载《伽达默尔集》,严平编选,第596页;另参见伽达默尔《伽达默尔论柏拉图》,余纪元译,第137-170页。
[12]伽达默尔与耶格尔有过接触和交往,参见伽达默尔《著作集》(德文版),第10卷,1995年,第405页。
[13]英译本:“Idea of the Good in Platonic-Aristotelian Philosophy”(《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善的理念》),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1986;法译本:“L¢Idée du bien comme enjeu platonico-aritotélicien”(《作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问题的善的理念》),Paris, Vrin, 1994。
[14]Gadamer, Idea of the Good in Platonic-Aristotelian Philosoph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2.
[15]参见阿尔法拉比《柏拉图的哲学》,程志敏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3-142页。
[16]Jean Grondin, Sources of Hermeneutic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p17.
3
沉思。它表明,晚年的伽达默尔同海德格尔的距离进一步拉大。
像其他两本书一样,该书也运用了现象学的描述方法。对于这一点更直接的影响来自于他的老师海德格尔早期运用现象学方法对亚里士多德的解读,伽达默尔特别重视柏拉图对话中具有暗示性却没有被明确表达出来的东西,在“去蔽”和“让-在”方面显示出他高超的解释艺术,这也是对他第一次听的海德格尔1923年夏季学期讲座、由后者所提出的一个现象学解释学原则——“解释学就是解构”(Hermeneutik ist Destruktion)[17]——的贯彻和应用;同时,也显示出伽达默尔对“古今之争”的态度:既不是站在假定古人优越的立场上,也不是站在假定今人优越的立场上,而是站在哲学解释学的“视域融合”的立场上来对待这一研究主题[18]。
二、柏拉图早、中期“善”的理念
苏格拉底无疑是柏拉图整个思想的起点[19]。这位将哲学从天上拉到地上的人,表明了哲学本质上是与人生密切相关的实践哲学,因为理论知识是从属于生活形式的;只要行动或实践是在特定的习俗和经济共同体中进行,因而从属于城邦(Polis)或国家,那它就是伦理学或政治学的[6]。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思想的特点有很精辟的概括:他只在与人有关的伦理学范围内通过归纳寻求普遍定义,而没有向外拓展,也就是将整个宇宙和人生统一起来,或者借用中国古人的话说在“天道”与“人道”的合一(即“天人合一”)的层面上将道德哲学与自然哲学统一于本体论和宇宙论、目的论,苏格拉底的伦理学立足于知识论,通过归纳追求普遍的定义,但这个普遍的东西,并没有与具体的东西相分离,成为实在的“理念”(或“相”)(《形而上学》,987b1-8,1078b27-32),而这正是后来柏拉图努力的方向,他要将苏格拉底的德性伦理学变成一种普遍本体论。
柏拉图《斐多篇》和《国家篇》是其前期理念论的代表作,通常人们对他的理念论的理解主要依据这两篇对话。但伽达默尔将《斐多篇》看作联结柏拉图早期对话和中期对话的中介[2](24),因为相对《国家篇》,虽然它首次引入了属于柏拉图自己思想的“理念”论,并显示出同晚期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联系,但这篇中期对话中苏格拉底的元素或成分更多一些。
伽达默尔尤其看重《斐多篇》所转述的苏格拉底的如下思想:受普罗塔哥拉“努斯”(nous)的影响,苏格拉底开启了“第二次航程”(“second voyage”)——“逃向逻各斯”(Flucht in die Logoi)[7],这在伽达默尔看来,意味着哲学开始走向以语言去追寻“理念”(或本质)的道路,从而成了“理念-哲学”(Eidos-Philosophy)[20],进而成了西方整个哲学的开端,无论对柏拉图本人的思想,还是对后来整个西方思想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8]。正是苏格拉底“德性即知识”的著名论断启发了柏拉图关于善的探讨上的“理智主义”立场。在他那里,辩证法与这种理智主义的立场分不开,它不是一种“科学”,而是“元科学”,它敞开作为理论科学的数理领域背后的东西,而柏拉图称辩证法为“phronesis”[21],《国家篇》中讲的四主德之首“智慧”有时用的就是它(有时也用“sophia”),显然我们不能将这里的“phronesis”译成后来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它在柏拉图那里相当于“智慧”(sophia)、“努斯”(nous),可理解为今天的“理性”(reason)[2](30)。但它也包括“实践智慧”或“实践理性”方面。
然而,柏拉图的《斐多篇》只是首次给出了“理念”世界,以区别于“现象”世界,而《国家篇》不仅如此,还突出了“理念之理念”,即“善”的理念,它是最高的理念,以区
--------------------
[17]海德格尔:《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何卫平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05页。
[18]参见Gadamer, Idea of the Good in Platonic-Aristotelian Philosophy, p.6;另参见拙译,载《伽达默尔集》,严平编选,第596-597页。
[19]严格来讲,这本书应当叫“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善的理念”,但由于苏格拉底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讨论他的思想离不开柏拉图的早、中期对话,故名。
[20]Gadamer, GW7, S.131.
[21]参见Gadamer, Idea of the Good in Platonic-Aristotelian Philosophy, p.35,37,41.
4
别于一切其他“理念”。伽达默尔强调,在柏拉图那里,“eidos”与“idea”属于同义词,经常可以互换,但唯独对“善”的理念,他只用“idea”,而不用“eidos” [2](27-28),表明这个词在其心目中具有独特的地位。
柏拉图的《国家篇》旨在建立一个“理想国”,一个政治的“乌托邦”,其手段是通过教育(最高目标是哲学教育)来实行统治或治理,这样它就由政治城邦走向了教育城邦,其核心问题是实现“正义”,而“正义”作为一种综合的“美德”(“德性”)同“善”分不开,于是追问“什么是正义”的问题,最终被归结为或转化为追问“什么是善”的问题,后者统摄前者。而且不仅于此,善的理念作为最高的理念(理念之理念),并非与其他理念相并列,而是一切事物的起点、根据、第一因。善的理念并不等于就是知识或真理[22],却是知识或真理的源泉或根据。
如果说苏格拉底对“善”的追问起始于“德性”,主要针对人的生活领域,而非是一种普遍的思考,那么到了柏拉图中期有了变化。无疑《斐多篇》《国家篇》都是沿着苏格拉底的方向围绕人的生活领域展开的,但柏拉图对“善”的反思具有了一种超越性,这尤其在《国家篇》中得到了明确的展现。此处的“善”成了统摄一切的原则,是一切事物的存在和可理解性的前提,柏拉图将其比喻为“太阳”来说明:它使万物得以存在,正如万物生长靠太阳;它还使万物具有可理解性,正如太阳发出的“光”照亮万物,让我们的眼睛(视力)能够看见一样,它既是可见世界的原因,又是可知世界的原因[23],西方传统的“光”的形而上学和视觉中心主义的源头可追溯至此。显然“善”这里的意义,不再仅仅局限于人生较狭窄的道德领域,而且还进入到普遍的本体论和基于此的认识论领域。也就是它由针对人的善最后发展成普遍的善,它指向一个目的论式的宇宙论(物理学),而后来的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式的物理学无非是沿着这一思路的进一步拓展和延伸[24]。
总之,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前期(或者说从柏拉图早期到中期),”善”的理念开始从具体走向抽象,从经验走向超越。《斐多篇》主要提出了不同于感性世界的理念世界,包括“善”的理念,而到了《国家篇》,不但提到了“善”的理念,而且还赋予它至高无上的地位,是所有其他理念的原因,因而是“理念之理念”。所谓“善”(good)就是“好”,它体现为一种价值判断,是非判断也要受制于它,它高于包括正义在内的其他所有德性或道德范畴,不仅具有伦理学的意义,还具有普遍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意义。
然而,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伽达默尔秉持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柏拉图整个思想是以苏格拉底的人的善为出发点的,然后上升到普遍的善(善的理念)(如《国家篇》),它可下降为相对于人的善的基础,而不是对二者的割裂。也就是说,并不是当代学界比较普遍理解的,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柏拉图割裂了实践的善和理念的善,后者成了外在的高高在上的东西,与接地气的善的具体实践却无法联系起来,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他前期所秉持的“分离说”造成的。显然,伽达默尔是不同意这种流行的观点的[25],他认为,总体上,柏拉图思想本身的发展是前后是连续的,而不是对立的。
三、柏拉图晚期《斐莱布篇》中善的理念
进入柏拉图晚期,善的理念作了进一步的推进,它以这个阶段的《斐莱布篇》为标志。施莱尔马赫称之为柏拉图最重要而又最难读的一篇对话[13],伽达默尔也十分重视柏拉图这篇对话,将其视为西方古代伦理学史上处于核心重要性的一篇对话[9],它是联结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中介,虽然它们关注同一个主题——“人生存中的善” [10],但
---------------------------
[22]这里的“知识”或“真理”是通过“理念”及其关系来体现的,属于理念世界,和“本质”相关联。
[23]参见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76页。
[24]参见Gadamer, Idea of the Good in Platonic-Aristotelian Philosoph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86-94.
[25]另参见伽达默尔《伽达默尔论柏拉图》,余纪元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第172页。
5
在伽达默尔眼里《斐莱布篇》具有特殊的意义,这就是设法摆脱“分离说”所带来的困境,朝着“善”的辩证理解——“善的辩证法”——推进,此乃进一步解决“多”中的“统一性”的问题所要求的。
我们知道,在《斐莱布篇》之前,属于柏拉图前后期“转向”的标志性对话《巴门尼德篇》借“老年巴门尼德”对“少年苏格拉底”的批评揭露出其过去的“分离说”困境,这种“分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理念”与“现象”的分离、“存在”与“生成”的分离。柏拉图晚期意识到了它所带来的困境:如果理念与现象是分离的,就无法解释现象如何“分有”理念,以及人如何能认识理念;如果“存在”与“生成”是分离的,就无法解释这个丰富变化的世界。这个批判对他后期辩证法思想的发展影响至深,它集中反映在《斐莱布篇》,这篇对话的贡献对其后来的思想产生了根本的“导向”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海德格尔在1924-1925年冬季学期的马堡讲座上曾预告过要阐释柏拉图晚期的两篇重要对话:《智者篇》和《斐莱布篇》,但最终只完成了前者,后者却付诸阙如[11]。几年后,伽达默尔做了这项工作,这就是他在马堡大学提交的教师资格论文,也是他的第一部专著,即:《柏拉图的辩证伦理学——对<斐莱布篇>的现象学解释》,而且是在海德格尔的指导下完成的,据说,海德格尔很满意[12]。对这篇对话的现象学解读不仅在伽达默尔的思想中具有开端性的意义,而且在他的第二部重要著作中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26]。
早期的《柏拉图的辩证伦理学》,主要探讨柏拉图对话意义上的辩证法如何与伦理学相关,这里伽达默尔关注的不是柏拉图的伦理学是辩证的,而是这种辩证法就是伦理学的[9](xxv),即辩证伦理学。其语言哲学的意味很浓,它突出通过对话达到“共同的理解”或“共享的理解”及其价值。伽达默尔认为,柏拉图的辩证法首先体现的不是纯私人性或孤独个体的反省活动,而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彼此交流、交往的共同体活动,即对话活动,在这种活动中,谁也没有权力说自己独占真理或者是真理的化身(例如像当时以“私人教师”身份出现的智者派所做的那样),他只能与别人平等地参与由逻各斯主导的对话,在这个过程中,只有那些经得起质疑和反驳的观点才有说服力,并被接受,进而被保留下来,真理唯有在这种活生生的交谈和讨论中才能获得并发展,人的知识和科学就是这样形成的,它促进人的共同体生活的一体性或社会理性以及社会道德的增长。
我们知道,《斐莱布篇》是柏拉图晚期最后一篇伦理学对话,其基本内容仍是探讨一个早就出现于之前的柏拉图对话中的苏格拉底式的主题:什么是善?对这个问题过去有两种回答:快乐或知识(参见《国家篇》,505b)。苏格拉底主张后者,而柏拉图早期大体上持他老师的立场。不过晚年的柏拉图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了改变,他提出了一种快乐与知识“混合”的善,这是他以前从未有过的观点。当然这种“混合”又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哪一种更接近“善”,是“快乐”,还是“知识”?柏拉图的回答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这样他与苏格拉底或他自己早期的观点又相去不远,仍保持着某种内在的联系,但同时又确实发展了苏格拉底的思想以及柏拉图自己的早期思想。注意,这里“快乐与知识”中的“知识”[2](105,108),柏拉图用的是“phronesis”,而不是“sophia”,而且是在人的生活的善的语境下,可见,它隐含有通向后来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知识”或“实践智慧”那个意思的端倪。
《斐莱布篇》提出了一个包括伦理学在内的普遍的本体论学说,它集中于这样一个基本论点:一切事物的存在含有四种类型(vier Gattungen):“无限”(阿派朗)[27]、“有限”(一)、这两者的“混合”和混合的“原因”。它们可归结为“有限”与“无限”的关系,“一”与“多”的关系,受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影响,将其数学化,也就是:“一”与“不定的二”的关系
----------------------------
[26]其实在我看来,柏拉图的《斐莱布篇》对于伽达默尔三专著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只不过在《柏拉图的辩证伦理学》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善的理念》是显在的,在《真理与方法》中则是隐形的。
[27]注意:这里的“无限”强调的不是那种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无限,而是指没有限定、没有规定、没有界限的意思。
6
(24b-c,31a,41d-e)[14][28],“二”的问题实际上指的就是“多”的问题[29],这里的“原因”(cause)可以溯源到《斐多篇》中的“努斯”(nous),它相对于《国家篇》中明确化的两个世界的分离说,是一个飞跃,它致力于“分离”与“分有”的调和或统一,展示了一种“理念”与“现象”的辩证法、“存在”与“生成”的辩证法[2](9-13)。它十分接近后来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和《物理学》中表达的“四因说”[30],以及“潜能”与“实现”的观点。
显然,柏拉图这里提出的存在的四类型说,是想进一步揭示理念论中“分离”与“分有”的关系。根据他过去的观点,现实世界只不过是理念世界的影像或影子,它是因为“分有”或“模仿”了理念世界才有自己的存在,至于如何“分有”或“模仿”,在柏拉图那里语焉不详,亚里士多德干脆说它们只不过是一种诗意的比喻。不过,伽达默尔注意到,柏拉图后期更多用“分有”(他自己的术语),而不是“模仿”(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术语),表明二者之间的差距。柏拉图试图要从逻辑上解决“一”与“多”的关系而用“分有”,这种“分有”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2](9-11)。显然,《斐莱布篇》包含对这一问题实质性的推进,其核心观点——一切事物存在的四个方面——让我们窥见到他后期思想中的伦理辩证法的发展[2](137-138)。
需要补充的是,虽然柏拉图晚年对自己的前期理念论进行了批判,但并没有导致他否定“分离说”的意义(亚里士多德亦如此),也没有因此而放弃理念论,他只是试图解决“分离说”的矛盾来完善自己以前的理念论。这一点在《斐莱布篇》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此处柏拉图所谓“有限”与“无限”的“混合”,也就是“一”与“多”的“混合”,“一”与“不定的二”的“混合”(16d)[15],而且这里的“混合”不等于简单的并置或堆积,而是按照一定的尺度、比例结合在一起而构成的具体事物,因此是不可分的整体,是被规定的实在(64d-e.),而其内在的“原因”(cause)就是“努斯”(nous)。世界上任何具体事物的存在都体现为这四个方面的统一[31]。
可见,伽达默尔前后期对柏拉图的《斐莱布篇》的理解保持了相当大的一致性。前期的《柏拉图的辩证伦理学》关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联系,因为《斐莱布篇》强调的不是两极或两端中的某一个,而是中道或中庸,如承认“快乐”和“智慧”(phronesis)相结合的“善”,这里含有辩证法意义的伦理学,它和后来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的主张有近似之处,后者追问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善是什么,而是对于人来说的善是什么,这种思想削弱了苏格拉底的德性与知识的同一,突出了辩证法与伦理学的同一,并指出了不可忽视的处境的具体性,在这个当中,人去判断什么对于他是善的并做出行动的选择[9](xvii)。
伽达默尔后期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善的理念》的第4章集中讲了“《斐莱布篇》中善的辩证法”。虽然这一章在全书所占的篇幅最小,只有区区二十来页,与带有结论性质的最后一章差不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重要,恰恰相反,它的作用是关键性的。只是因为它的主要内容在前期的《柏拉图的辩证伦理学》中已经涉及到,所以这里没必要过多重复。在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为《柏拉图的辩证伦理学》写的第3版序言(1982年)中,已步入耄耋之年的伽达默尔仍承认这部处女作重新再版具有意义,其基本内容是站得住脚的[9](xxxiii)。
作为伽达默尔思想真正开端的《柏拉图的辩证伦理学》主要探讨了两个问题:善的理念的实践性和辩证法何以就是伦理学。它包含政治学,并通向他后来明确创立的哲学解释学。伽达默尔在这里强调对话本身就是生活的伦理方式,合理性的东西不是现成的,也不是由哪一个人决定的,而是在对话的辩证过程中寻觅到的。伽达默尔十分看重柏拉图的这种对话理
----------------------
[28]参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1卷,第6章;另参见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卷2,人民出版社,1993年,1128-1129页,1144页。
[29]参见伽达默尔《伽达默尔论柏拉图》,余纪元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第145页。
[30]这里“无限”相当于“质料”,“有限”相当于“形式”,“混合”相当于质料与形式的统一所构成的具体事物,而“原因”相当于动力因、目的因和形式因。
[31]参见Gadamer, Idea of the Good in Platonic-Aristotelian Philosophy, p. 29,15,114,122.
7
性,即在对话过程中寻求合理性,并将它和亚里士多德所突出的“实践智慧”联系起来,其意义具有普遍性。这样对话、辩证法和伦理学达到了一致。
作为伽达默尔第二部重要著作《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善的理念》也着重讨论了《斐莱布篇》中的“辩证法”,但主要是围绕着辩证法与“善”的理念的联系展开的,这里的辩证法体现在这一认识中,即:与人相关的善既非单纯的“智慧”,也非单纯的“快乐”,而是二者的“混合”而成的一个第三者。“善”在这里不再是抽象的、外在的、具有某种神秘意味的东西,而是与“美”结合在一起,与“尺度”和“适度”联系在一起,从而成了具体的、可感的存在,进而达到被“爱”(喜欢)。总之,善要从美的事物中显现出来(它在那里)、被看到,这就是善与美的结合,因为美存在于可见事物之中,只有在美之中发现善[32]。
注意,柏拉图在《斐莱布篇》中不仅提到了将“快乐”与“智慧”混合的善[2](110-111),还提到了作为这种“混合”之“原因”的善(64d)[2](114-115)——它基于这样一个公理:一切事物的产生都是有原因的(26e)。是“善”的原因造成了具体的善,它涵盖“人之善”与“宇宙之善”(64a)[33],而这一点通向柏拉图后期的《蒂迈欧篇》。《蒂迈欧篇》是《斐莱布篇》所提出的存在的四类型说的进一步展开,用中国传统的话来讲,前者偏向于“天道”,后者偏向于“人道”,天人合一,从而使“善”具有了一种普遍的本体论意义了,它作为“努斯”(nous)意义上的“原因”,指向一个理性“神”,是它造成“有限”与“无限”的混合、“一”与“多”的混合,或“一”与“不定的二”的混合,从而形成了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万事万物,包括由“快乐”与“知识”之“混合”而构成的具体的善的生活。
这里提到了“宇宙灵魂”(或“世界灵魂”)——它是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通过一种由近及远的类比推理得到的:我们拥有身体,我们的灵魂寓于身体之中,这个身体的成分与宇宙身体的成分相同,并且是由宇宙的身体所供养的,我们不能设想这个拥有与我们的身体同样元素并且在各个方面都要完美得多的宇宙没有一个灵魂,否则无法说明我们的灵魂是从哪里来的[34]。这里就含有后来《蒂迈欧篇》所明确了的“人的灵魂”与“宇宙灵魂”(“世界灵魂”)关系的说明,这个宇宙灵魂就是智慧和理性的寓所,它一方面提供身体的元素;另一方面提供理性的尺度,所以产生一切事物作为第四种东西的原因包括理性、智慧和灵魂(《斐莱布篇》,30a-d)。这里“原因”被归结为“制造者”或“创造者”(26e-27a)(它就是柏拉图表述的“德穆革”)。虽然在总体上《斐莱布篇》主要是探讨“人之善”,并没有去分析“宇宙之善”,但暗示了这一方向,并表明二者是同一个善[35],它由后来的《蒂迈欧篇》完成。它们预设于《斐多篇》提到的“灵魂”、“城邦”(国家)和“世界”三个领域中。这里由柏拉图的三篇对话代表了“善”的发展:《国家篇》《斐莱布篇》和《蒂迈欧篇》[36]。
按照伽达默尔的理解,《斐莱布篇》与《蒂迈欧篇》这种关联对应于后来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与《物理学》的内在关联[2](114-115),实际上还应包括《形而上学》,而柏拉图具有普遍本体论意义的“善”的理念与亚里士多德的“神”的理论相契合,神(理性神)或努斯代表最高的善[2](152),由此就可以看出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只不过柏拉图的表达更带神秘的比喻性,而亚里士多德将其概念化了,并赋予了更多的逻辑论证。
作为个人生活的善或好(good)在古希腊都被定义为幸福。在《斐莱布篇》中,柏拉图关注到个人的幸福。也就是说,这里的幸福与个人的善或好有关,但快乐和知识哪一个更接近善或好?如前所述,柏拉图的回答仍然没有偏离苏格拉底的路线——知识。由于柏拉图在
------------------
[32]参见Gadamer, Idea of the Good in Platonic-Aristotelian Philosoph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15-117.
[33]柏拉图在《斐多篇》(98B)中就谈到了“宇宙之善”。
[34]现代生命科学早已经打破了有机与无机的界限,对古老的身心关系作了深刻的推进,它进一步证成,意识是有物质基础的,正如一位天文学家所说,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原因在宇宙的深处。柏拉图早已以他自己的一种朴素的方式扑捉到了这一点。
[35]参见Gadamer, Idea of the Good in Platonic-Aristotelian Philosoph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12.
[36]伽达默尔《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间的善的理念》,德文版,第214-215页。
8
这里集中讨论了什么是快乐,因此这篇对话又被公认为是“论快乐”的对话,他在其中使用了辩证法来揭示快乐的本质,它显然不是纯肉体上的,而是精神上的,更接近审美的那种愉悦。它预示了后来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幸福”,《尼各马可伦理学》(第7卷、第10卷)也专门谈到过“快乐”的问题,以及“快乐”与“幸福”的关系,同柏拉图这里讲的有得一比。
总的来说,柏拉图晚期的《斐莱布篇》进一步提出了统一两个世界的本体论,它包含两种善:一个是具体的善——快乐与理性相结合的善;另一个是根本的善——作为“原因”的“努斯”意义上的最高的善(至善),它是使其他一切善的事物之为善的原因,别的事物因为“分有”它或相似于它而为善,它通向神,即理性神[后来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第12卷)将其明确地表述为“第一推动者”],它是对古希腊神话中的“诸神”的超越(这在柏拉图《国家篇》关于诗与哲学之争就表现出来了)。这两种善是统一的,而非分离的。显然,相对于《国家篇》中那个最高、抽象空洞的善,善在《斐莱布篇》中变得比较具体了[16](1087),至此,“多”与“一”的统一性得到了加强,“分离说”虽然不能说已经放弃了,但至少它所造成的张力得到了削弱或缓解,促进了对“善”的问题理解的辩证深化。
四、从柏拉图的自我批判到亚里士多德的批判
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善的理念》中,伽达默尔多次强调,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批判与柏拉图后期的自我批判具有某种相似性,这只要拿《形而上学》与《巴门尼德篇》对比一下便不难看出,例如著名的“第三者”的论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2)。毕竟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学园呆了20年,当他刚进入学园时,柏拉图的思想已经进入到晚期,已经开始对前期的理念论的不足进行批判了,亚里士多德不可能不了解老师的这种批判并从中受到启发。如果只考虑柏拉图中期的理念论(以《斐多篇》和《国家篇》为代表),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差别确实比较大,但如果将柏拉图晚期思想纳入进来(主要有《巴门尼德篇》《斐莱布篇》和《蒂迈欧篇》)并与前期思想对接(主要有《斐多篇》《国家篇》),二者的差别不仅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而且恰恰证明了两人思想的关联[37]。
不难看出,柏拉图前期,毕达哥拉斯学派和埃利亚学派(主要是巴门尼德)对他的影响最大,比较排斥赫拉克利特,而柏拉图后期较多融入了赫拉克利特的“生成”(变易)的思想,并加以调和,别开生面。他晚年已经提出了超越“分离说”的四类型统一的存在论(即存在的四类型说),后来的亚里士多德建立的质料与形式相结合的统一世界观显然是其进一步的发展。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无论亚里士多德怎样批判柏拉图,在伽达默尔眼里,他仍然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而且是第一个柏拉图主义者,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这个基础是由柏拉图奠定的。例如,亚里士多德追随苏格拉底-柏拉图的“逻各斯转向”,秉持的“理念-哲学”或“爱多斯-哲学”(Eidos-Philosophie)[38],而且伽达默尔认为,柏拉图的“理念”并非亚里士多德刻板认为的那样是与具体“现象”是完全分离的,实际上,理念是现象的理念,他的“分离说”并非要切断这样一个预设的关联,他的“分有说”就暗示了这一点。造成“分离”这种错觉的是柏拉图基于数学的立场,而亚里士多德是基于物理学立场:数学代表的是纯粹理智的东西,但后来自然科学的数学化或数学的自然科学化的发展(以近代早期的伽利略、刻卜勒为标志)表明了这种表面的“分离”实际上并非如此,数学的自为存在与“现象”之间有着一种生产性的关系[39],这一点早在柏拉图晚年的物理学或宇宙论(《蒂迈欧篇》)中就得到了预示,在那里,柏拉图用数学(立体几何)来解释物理现象;而亚里士多德对此比
------------------------
[37]参见Hans-Georg Gadamer, GW7,S.131.
[38]参见Gadamer, Idea of the Good in Platonic-Aristotelian Philosoph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61. 另参见Hans-Georg Gadamer, GW7,S.131.
[39]我们今天的“大数据时代”进一步表明了这一点。
9
较抵触(他视柏拉图为一位毕达哥拉斯主义者[40]),而他自己主要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认识普遍和个别的关系。不过,即便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善”也被刻画为“一”,它体现为多样性的统一性,是最高的知识,先于其他一切知识,例如,伦理学与物理学。这和柏拉图前后期一贯的思想保持一致[41]。
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伦理学,在这里,他认为柏拉图普遍存在论意义上的善与相对于人的具体生活实践中的善过于抽象、空洞,无法相容,而伽达默尔认为,这正是柏拉图的《国家篇》中所遭遇到的问题,而最后走向辩证法的上升道路。与之相关,伽达默尔洞察到,亚里士多德不仅是伦理学的奠基者,也是物理学的创始人,而在他那里,善既体现于伦理学之中,也体现于物理学中,前者继承了苏格拉底的遗产,体现为属人的善,后者实现了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实则柏拉图自己)的要求,体现于事物存在的“四因说”中的“目的因”(这里的目的因就是善),两者统属于一个整体,不可割裂。而且由目的因指向终极因,与神性联系起来,最后的善在物理学之外,属于第一哲学[42]。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对伦理学之善(进而实践哲学之善),即属人之善的追求,回避不了对作为善的存在之共同性——善本身,或善的理念的问题,善既包括人类的实践领域,也包括超越人类实践的领域,它涉及到黑格尔明确表达的“具体的普遍”,对此“分离说”是一种误导[43],经过伽达默尔的分析,亚里士多德针对柏拉图分离说的批评,并未示远离柏拉图的思想,反而说明了他与柏拉图晚期对话的亲缘性[44]。可见,这里又涉及到伽达默尔对以往流行的对柏拉图理解的一种矫正。
然而,伽达默尔仍很看重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善”的理念的批判,因为这也可视为是对柏拉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而正是这一点将伽达默尔引向了普遍解释学的深处。值得一提的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善的理念》第5章显然吸收了伽达默尔的文集《对话与辩证法》的最后一篇:“我爱柏拉图,我更爱真理”[5](212-238)中的观点,后者曾作为附录被收入到《柏拉图的辩证伦理学》第2版(汉堡,1968年),由此可见它们之间的关联。其实,这篇论文更突出的是“我爱柏拉图”,以说明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之间密不可分,而不是对立。但对伽达默尔而言,亚里士多德批判柏拉图“分离的”善的理念毕竟不是多余的。
其实,伽达默尔的第一部重要著作《真理与方法》就谈到过这种批判,只是没有提到这种批判与柏拉图晚期的自我批判的联系,而且也比较零碎,没有详细、集中的展开,不过关键之处都已经点到了:
亚里士多德在探讨善的问题时限制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智主义”(Intellektualismus),从而成为一门独立于形而上学学科的伦理学创始人。亚里士多德批判柏拉图的善的理念乃是一种空疏的共相,他以对人的行为来说什么是善这个问题取代了[一般]的善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这种批判的方向证明,德行(Tugend)和知识、“德性”(Arete)和“逻各斯”(Logos)的等同——这种等同乃是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德性学说的基础——乃是一种言过其实的夸张。……伦理学(Ethik)这一概念在名称上就指明了亚里士多德是把“善”建立在习行(Ubung)和‘Ethos’(习俗)基础之上的这一关系[45]。
伽达默尔的第二部重要著作《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善的理念》与第一部重要著作《真理与方法》的上述观点保持着一致,但作了更加深入、细致、全面的展开(详见第5章)。在这里,伽达默尔集中分析了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善”的理念的批判,他主要依据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三个文本——《尼各马可伦理学》《大伦理学》和《欧德谟伦理学》—
------------------------
[40]参见伽达默尔《哲学的开端》,赵灿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5页。
[41]参见Gadamer, Idea of the Good in Platonic-Aristotelian Philosoph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31-32.
[42]参见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卷3,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55页。
[43]参见Gadamer, Idea of the Good in Platonic-Aristotelian Philosoph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28-130。
[44]参见Gadamer, Idea of the Good in Platonic-Aristotelian Philosoph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39-140。
[45] 伽达默尔:《诠释学I: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24页。译文有改动。
10
—来进行的,尤其看重其中的《欧德谟伦理学》,因为后者这方面的内容最多。
伽达默尔注意到,这三个文本开头部分都针对柏拉图“善”的理念进行了批评,认为柏拉图关心的是“善”的理念与一般本体论的联系,而不是与人的实践哲学的联系。亚里士多德则明确强调善的意义是多重的,它和存在的意义一样多(《欧德谟伦理学》,1217b26-1218a1),他本人所关注的是相对于我们的善(即相对于人的善),而不是绝对的善或神的善;是可以实践的善,而不是不可实践的善。前者属于实践哲学要讨论的,后者属于第一哲学(神学)所要讨论的。如果善是分离的,独立自在的,那么它就既不能为人所认识,也不能为人所实行,从而在人的生活实践中是无用的(《尼各马可伦理学》,1096b30-1097a10,1217b25),所以亚里士多德一再讲,在伦理学中他不讨论柏拉图空洞、抽象意义上的善的理念,只讨论与我们的实践相关的具体的善(《大伦理学》,1183a30-38),以消除柏拉图“善”的理念的外在的超越性或超验性(transcendence)。这似乎表明,经过了柏拉图之后的亚里士多德要在一个更高层次上回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前期)的传统——善是实践的善[2](128)。
上述观点基于亚里士多德相对“他眼里的”柏拉图中期的“分离说”的超越,这表现在其“实体说”中。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第一实体”与“第二实体”的关系不是分离而是统一的,第一实体是基础,第二实体寓于其中,而不是与之相脱离,这就是他著名的“这一个”(tode ti)与“是什么”(或“什么是”)(ti estin)之间的关系。从形式(eidos)与事物是不可分的前提出发,他不认为善是外在于一切事物、独立自在的、自为的、超越于一切实存,而是存在于所有善的事物中那个共同的善,这体现为一种“具体的普遍”[46],它与柏拉图抽象的普遍——善的理念不同,后者的“善的理念”与具体是分离的(《大伦理学》,1128b10-15)。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讲,柏拉图的“善”是外在的(唯实论意义上的),而亚里士多德的善是内在的,它们是两种不同意义的善,进而由此显示出两人的重要区别[2](132)。亚里士多德用“多之中的一”取代了柏拉图的“多之上的一”[47]。
不过,如前所述,柏拉图后期已经意识到了“分离说”的困境,并试图解决之,《斐莱布篇》《蒂迈欧篇》就代表了这一方向;至于亚里士多德十分重视学科的划分,强调的是“对于我们的善”(good for us)(即对于人的善),而不是“对于神的善”(good for the god),那么它就应是实践哲学(最高是政治学)的对象,而不是第一哲学(神学)的对象。可是,柏拉图在《国家篇》中就触及到了“对于我们的善”(505b),或者说具体的善(是从它出发的),更不用说后来的《斐莱布篇》了[2](147-148)。然而,即便“对于我们的善”也意义繁多,且与普遍性相关,这种共同的善往后追溯来自一个东西,那就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作为“第一推动者”的神或努斯(理性),它体现了最高的善,显而易见,它与柏拉图《斐莱布篇》中那个作为 “原因”(cause)的“努斯”(nous)有继承关系。可见,无论在柏拉图,还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善都是多义的,或同名异义的,例如,它有伦理学的意义,物理学的意义,还有第一哲学的意义,由这里也可以看到,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关联。
值得强调的是,亚里士多德虽然进行了学科划分,但并不意味着他要放弃这些学科之间的联系,何况他也讲过,具体的善要服从最高的善,个别的善要服从整体的善, “总体的善比特殊的善更值得选择”[48]。这样,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又非常相似了,他只不过以更加概念化的方式论证了整个世界的目的论秩序,而这正是柏拉图《斐多篇》中的预设,后者提到的三大领域——灵魂、城邦(国家)和世界——贯穿着一个统一的善,而亚里士多德同样关心整个宇宙的统一,正是在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分享了柏拉图的世界观[2](155)。只是柏拉图基于数学的立场,亚里士多德基于物理学的立场,后者赋予物理学比数学更优先的地位,他总是从具体的事物——“这一个”出发,然后去追问它“是什么”(本质、定义),由于这
------------------
[46]伽达默尔这里借用黑格尔更加明确的具有辩证意义的表述。参见GW7, S.202.
[47]参见爱德华·策勒《古希腊哲学史》,第4卷(上),曹青云译,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22页。
[48]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01页。
11
一差别,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形式是在事物的显现中被经验到的,而不像柏拉图那样是在反思中得到的”[5](237),具体到伦理学也是如此。相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更接近现象学家的立场,这恐怕是海德格尔前期非常重视他而不是柏拉图的一个重要原因,受其影响,在前期,伽达默尔也是比较倾向亚里士多德的。
五、实践哲学与哲学伦理学
伽达默尔研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善”的理念的关系时,注意到在古代,理论和实践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理论被看作是最高的实践,是人存在的最高方式[17],没有像现代割裂得那样厉害。当然伽达默尔也指出,实践哲学本身是理论而不是实践,不是实践智慧,它具有理论的特征,只不过它不是一般的理论,而是关于实践的理论,要用于实践[49]。这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表现得非常明显,不过,实践哲学与实践智慧(phronesis)的内容分不开。但我们在柏拉图那里是找不到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实践智慧”那种用法的,柏拉图虽然也使用“phronesis”这个词,但却是广义的,它包含“理论知识”和“技艺知识”,而不只是亚里士多德后来所限定的“实践知识”或“实践智慧”,柏拉图经常将它与“sophia”(智慧)混用,而后来的亚里士多德对“sophia”和“phronesis”作了严格区分:前者指“理论智慧”,后者指“实践智慧”。无论苏格拉底,还是柏拉图都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明确地做到这一点,这是他在西方哲学史乃至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贡献。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上述划分,实践哲学不再涵盖形而上学、物理学的内容,实践智慧远离普遍的目的论,但这种做法也产生了一个问题:作为特殊的实践哲学(包括伦理学与政治学)同理论哲学(如形而上学、物理学或本体论、宇宙论)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如前所述,亚里士多德的学科划分在历史上是一个进步,但也容易造成一个误区,仿佛它们是割裂开的,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亚里士多德的本意,他仍然要统一地看待它们,认为一切认识最终要追溯到“本原”或“第一原则”,此乃哲学彻底性的要求,这又与柏拉图是一致的,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有天人合一、宇宙人生不分的一面。
值得注意的是,伽达默尔在这里还专门提到康德那本“伟大的小书”——《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的第1章“从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识过渡到哲学的道德理性知识”,实际上是要突出书名中的形而上学的“奠基”,它显示为追求一种普遍的有效性[50](因为在康德眼里,“没有这个形而上学就根本不会有任何道德哲学”[51])。这样就将西方近代的康德也纳入到古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共同主题和统一效果的传统中来了。
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是在批判柏拉图“善”的理念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实践哲学的。他所提及的理论生活与实践生活与柏拉图的哲学生活与政治生活有着渊源关系[52],对应于他所谓的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亚里士多德眼里的最高认识之可能性来自于“努斯”(nous),它既可归属到理论知识,理论智慧(sophia),也可归属到实践知识,实践智慧(phronesis),它们是同一理性或同一智慧的两个方向[2](171),正如在康德那里,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不是两种理性,而是一种理性,是同一种理性的两种不同的应用一样。伽达默尔在这本书中通过对亚里士多德的这种解释,明确地要将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统一起来,这可视为伽达默尔晚年思想的一个重要进展。因为在此之前的《真理与方法》没有做到这一点,主要体现为一种矫枉过正,比较突出的是“实践知识”或“实践智慧”。
如前所述,柏拉图《斐莱布篇》所提出的存在的四类型说包含有具体的善(“混合”的
------------------
[49]参见Gadamer, Idea of the Good in Platonic-Aristotelian Philosoph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60-161,163.
[50]参见Gadamer, Idea of the Good in Platonic-Aristotelian Philosoph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70-171;另参见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杨云飞译,邓晓芒校,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1-29页。
[51]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杨云飞译,邓晓芒校,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页。
[52]参见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80页。
12
善)和最高的善(“努斯”的善),后者是前者即“混合”的善产生的“原因”,这样看来二者在柏拉图那里是统一的。虽然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涉及具体的善,要避免从普遍性的角度去谈最高的善(至善)——那是第一哲学(形而上学)和第二哲学(物理学)的事情,但由于人的生活离不开自然,定位于世界或宇宙之中,人的生存即他的活动最终超越它自身而指向神[2](171-172),这可以说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并不是完全脱节的。在他那里,实践哲学作为人的哲学,主要包括伦理学和政治学,而理论哲学主要包括数学、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神学)。这样,他与柏拉图仍是“近邻”,相去不远,根据伽达默尔,更确切的表达是二者的同一性和统一性。
接下的问题是:就人而言,对应于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的两种生活——理论生活与实践生活——孰高孰低?无论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作了一致的判断:前者最高(《斐莱布篇》20d;《尼各马可伦理学》1177a15-1178a7)。即便是带有混合性的实践生活,其中的理性或精神的因素也被看得更重。只是相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表达得更加明确:第一好的生活是理论生活,这是神的生活,但人不是神(不死者),而是有死者,因此不可能完全过这种生活,他只是“爱智慧”(philosophia)——追求智慧,而不是占有智慧(sophia)[53]。于是有一个“第二好”的生活,这就是人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生活[54],也就是柏拉图《斐莱布篇》中所说的“快乐”与“知识”(理性)相“混合”的生活,这里“混合”意味着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复合体,“混合”不是随意的,而是要混合得好,而不是混合得糟(61b),这就离不开“理性”的介入与支配,此处的“混合”包含尺度、美和真理,可以说,它就是真善美的统一[2](31,115,117,124-125),由于结合了尺度、比例——理性,这里的“快乐”就成了一种精神性的愉悦,它体现为一种美感,而非单纯肉体或生理上的快适,它通向后来亚里士多德的“快乐”乃至“幸福”。这也表明,“善”本身是看不到的,它只通过美的尺度和比例方能显现出来[55]。
不过也毋庸讳言,这里伽达默尔作了一些自己的阐发。他认为,亚里士多德所谓实践生活是“第二好的”,并非含“次一等”的意思,而是两个最好的生活之一,它们相互隶属,一起构成人的善的生活,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性生活。这样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那里,善显现为一种目的,它不仅指向人类,还指向整个宇宙,这个宇宙被理解为趋向至善,按照苏格拉底的说法,“宇宙是根据我们的道德经验来理解的”[56]。后来康德的三大批判从认识论出发,最终通过目的论走向道德本体论与之有相似之处。而这种具有本体论(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正是伽达默尔要从解释学角度加以发挥的。
他的解释学作为实践哲学,其重心在伦理学,通向政治学,二者本来在古希腊就密不可分,伦理学只是政治学的一部分(或者说,伦理学是缩小了的政治学,政治学是扩大了的伦理学)。亚里士多德在《大伦理学》中一开头就明确地讲,他这里要讨论的并非道德是不是知识的问题(苏格拉底-柏拉图),而是道德是什么样的知识(亚里士多德),他的回答不是精确的理论知识,而是严格的实践知识;它不仅包括伦理学,还包括政治学,它所指的是实践哲学以伦理学为起点、以政治学为终点的那个意义[18],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将德性的研究最后隶属于政治学(1102a10-15)。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作为实践哲学也是这个方向,这在他的第二部重要著作《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善的理念》被进一步暗示出来了。这里它既提到“实践哲学”,也提到“哲学伦理学”[2](166-169),由于伦理学是其中的基础与出发点,所以伽达默尔谈实践哲学时提及伦理学要比政治学多得多,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学不重要。同古代哲人一样,政治学被他视为“最高的科学和艺术”[2](166)。
--------------------------------
[53] 这个表达与后来的黑格尔相反。参见Gadamer, Idea of the Good in Platonic-Aristotelian Philosophy, p.xxviii, 176.
[54] 对于大多数人来讲主要过的是实践生活,因为从事专业理论的人(典型的如哲学家)毕竟是少数。
[55]参见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Gadamer, ed. by Bobert J. Dosta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218
[56]Gadamer, Idea of the Good in Platonic-Aristotelian Philosoph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xxix.
13
其实,这一点在《真理与方法》中就有所涉及。伽达默尔指出,他真正感兴趣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的遗产和亚里士多德的习俗(Ethos)之间的协调关系,这集中表现在他们各自对”善”的理念的理解上。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柏拉图这方面既有批判,又有保留,例如,苏格拉底强调知识是道德存在的本质要素,这个方向不仅是柏拉图要坚持的,也是亚里士多德要坚持的,但亚里士多德补充进“实践知识”和“实践智慧”,它是一种面对可变事情的选择,这里面就包含有具体的善,而不是柏拉图所讲的纯粹理智的、脱离实际的抽象、空洞的善。这种善不仅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行动,它要考虑到具体处境。就这一点看,道德知识与解释学可以达到某种一致,而且道德知识就是与人相关的实践知识,由此发展出道德科学,而在西方观念史上,“道德科学”(moral sciences)曾经是人的科学——精神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代名词,这种表达我们在休谟、穆勒(密尔)等人的著作中就可以看到,直到19世纪后半叶它才逐渐被“精神科学”所替代[8](11-12)。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与这种基于道德科学的精神科学相联系,这也可看成是基于海德格尔的前提,通过布尔特曼,回到施莱尔马赫、德罗伊森和狄尔泰的传统。
伽达默尔注意到,亚里士多德虽然继承了苏格拉底的传统,强调道德即知识,但他认为,这种知识不应当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强调的一种纯粹理智的领域,即理论知识,而是实践知识。前者与不变的事情有关,这类知识在古代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数学;而后者与可变事情有关,和人的习俗有关,同人的行动分不开,最典型的代表是伦理学。这里伽达默尔似乎将“实践智慧”(phronesis)和“实践理性”(praktischen Vernunft /practical reason)或“实践的合理性”(praktischen Vernunftigkeit /practical reasonableness)作了某种等同的使用[57],并强调要建立一门哲学伦理学,这种哲学伦理学与他的哲学解释学目标一致,而且再次提到了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2](165),这同他本人另外一篇重要论文《论一门哲学伦理学的可能性》(1963年)所表达的思想可联系到一块来理解。与《真理与方法》相比,后者对康德的赞同多于批评,在这里,伽达默尔也像舍勒一样表达了对康德的充分尊重,但又能正视其不足,予以补充。
与柏拉图相比,亚里士多德主张善的具体化、多样化,它既包含世俗的善,也包含超世俗的善;既包含质料的善,也包括形式的善。我们知道,舍勒区分了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和质料的价值伦理学,如果说康德是前一类最典型的代表,那么亚里士多德则是后一类最典型的代表。伽达默尔的老师尼古拉·哈特曼在他的《伦理学》一书中就明确地讲过,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含有丰富的质料价值伦理学的内容[19]。伽达默尔前期主要站在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立场上力图在解释学领域中恢复古代实践哲学传统,而后来则愈来愈有一种融合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倾向,认为两者都不能独善其身,它们不应是对立的,而应是互补的[2](97-98),并将这视为他所设想的一门未来可能的哲学伦理学的发展方向,也就是要将伦理学的质料主义与形式主义结合起来,扬弃二者各自的片面性,这显然是一种辩证的方向,此方向可以说有舍勒的启发,虽然舍勒所要建立的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不同于尼古拉·哈特曼所理解的亚里士多德的质料的价值伦理学[20]。
伽达默尔认为,康德强调道德律是无条件性的绝对命令不乏追求道德纯洁性和严格性的积极一面,但有其局限。它总体上是形式主义的,体现为一种刚性的普遍原则,只强调从“善良意志”出发,不考虑行动的质料,不考虑“例外”,不考虑根据具体情况的变通,不看重实践智慧,因为实践智慧(明智),在康德眼里,基于人的福利考虑,所以它的行为准则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假言命令[21],而不是定言命令,这最终导致康德对实践智慧不重视,从而在其道德原则的应用上显得苍白无力,在这个方面任何为康德做辩护的努力似乎都近乎徒劳,因为这是他的义务伦理学本身的问题(黑格尔早就批判过);而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也
-----------------------
[57]参见Gadamer, Idea of the Good in Platonic-Aristotelian Philosophy, p.166,171,175. 另参见伽达默尔《诠释学II: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第27页、590页、611页。
14
强调从“善”从发,但突出实践智慧,主张要考虑具体情况或处境,强调条件性[17],有其深刻、合理的一面,但它也有容易导向康德眼里的道德机会主义[58]、功利主义,乃至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一面。
康德与亚里士多德的对立在这里突出的尖锐问题是:在道德实践领域,只讲定言命令,不讲假言命令行不行(实践智慧体现的就是一种假言命令)?或者反过来,只讲假言命令,不讲定言命令行不行?恐怕都不行。我认为,晚年的伽达默尔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要调和亚里士多德和康德,走另外一条道路,也就是第三条道路,即:既不完全是康德式的,也不完全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其实也就是要解决一个形式与质料的统一问题),它体现出伽达默尔哲学伦理学的一种辩证倾向,表现为一种黑格尔主义的立场,但如何将这两个不同的伦理学具体地统一起来,尚未见到其详细、充分的论证,我们需要深入地研究,然后接着讲。笔者认为,这里隐含有这样的可能性:伽达默尔似乎要将康德的“绝对命令”转化为“一般命令”,也就是要考虑到“例外”,考虑到“实践智慧”,在保持道德原则的“刚性”的前提下面留有“柔性”或“弹性”,而这又不至于导向相对主义,因为伽达默尔用康德来弥补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本来就包含对这一点的避免,同时这也是要与功利主义划清界限[22]。
结 语
综上所述,伽达默尔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善的理念》这本书的基本观点集中表达了两点:1.柏拉图自身思想的连续性;2.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思想之间的统一性。它超越了德国的新康德派和耶格尔派,以及海德格尔的挑战。新康德派看重柏拉图而贬抑亚里士多德,而海德格尔看重亚里士多德而贬抑柏拉图,将柏拉图等同于柏拉图主义,将柏拉图主义等同于遗忘存在的传统形而上学,是应当被克服的对象[59],而且海德格尔本人对柏拉图的解释也主要是从亚里士多德出发的(如关于《智者篇》的讲座,这本讲柏拉图的大书前面几乎花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在讲亚里士多德)[11](23-308),而耶格尔基于西方19世纪以来的“发展观”来研究亚里士多德,将其思想的形成史看成是走出柏拉图的历史,至于伽达默尔本人早期第一部著作《柏拉图的辩证伦理学》,也主要是从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7卷10-13章、第10卷1-5章)中论“快乐”的立场出发去解读柏拉图《斐莱布篇》的,所以他自己后来称它为一部“未明说的关于亚里士多德的书”[22](594),或者说,是为这样一本书做准备的,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它与海德格尔《柏拉图的<智者篇>》的某种相似性,而且在表达上深受前期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
伽达默尔晚年著作《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善的理念》不再受这种影响——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对立来看。在他眼里,柏拉图的思想具有连续性,这种连续性既表现在柏拉图的前后期思想,也表现他与亚里士多德的关系上。亚里士多德虽然批评柏拉图,但仍然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而且是第一位柏拉图主义者[60],因此,不仅要从亚里士多德去看柏拉图,更要从柏拉图去看亚里士多德,以把握二者的“统一效果”,他们一起构成了整个西方思想的“开端”,并决定了后来的“保持”[61]。伽达默尔晚年思想的发展恰恰是要重返这个“开端”,这一点他与海德格尔(还有胡塞尔)的思想轨迹一样:向前进就是向后退,即所谓“返回的道路”。只不过海德格尔要返回到前苏格拉底,而伽达默尔要返回到柏拉图。
-----------------
[58]参见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76页、377页。
[59]参见Gadamer, Idea of the Good in Platonic-Aristotelian Philosoph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5.
[60]参见伽达默尔《伽达默尔论柏拉图》,余纪元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第172页;另参见伽达默尔《诠释学II: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614页。
[61]海德格尔喜欢引用荷尔德林的说法:“你如何开端,就将如何保持”;伽达默尔喜欢引用黑格尔的说法:开端是终结的开端,终结是开端的终结(参见伽达默尔《诠释学I: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636-637页;另参见伽达默尔《诠释学II: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41-442页)。这对当年德国图宾根大学的室友此处所表达的思想其实是一致的。
15
20世纪以来,西方解释学的确有一个实践哲学的转向,或者说,伦理学的转向,这在当代哲学解释学的创立者——伽达默尔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尤为典型。他明确地讲,解释学就是实践哲学,而实践哲学的核心就是“实践智慧”与“善”的理念,而“实践智慧”(phronesis)离不开“善”、隶属于“善”,是对善的具体追求和应用,它必须要考虑到特定的处境(在这个过程中去把握什么是“好的”或“恰当的”,它不同于“聪明”(cleverness),因而也不同于专家的工作和技术的应用,尽管在广义上,亚里士多德有时也将技艺活动看成是一种实践);另外,由实践智慧把握的具体的善又要有形而上学的前提和基础。伽达默尔这本书通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善”的理念的处理揭示了实践哲学与存在哲学的关系,暗示了哲学伦理学与哲学解释学的联系,它让我们想到从苏格拉底经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所展示出的这样一个思想: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是从我们的道德经验出发的,它基于什么是善或好[2](xxiv-xxv),同时它总包含有未来超越性的一面,这进一步表明,解释学绝不仅仅是一个方法的问题,技术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存在的问题,意义的源头归根结底在于善的追求。
如果说,实践哲学贯穿于伽达默尔的整个学术生涯的始终,那么可以说,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真理与方法》突出的是“实践智慧”,那么他的第二部重要著作《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善的理念》突出的是“善”的理念。伽达默尔明确地讲,“实践智慧”这个问题在《真理与方法》中占据了核心地位,该书所描述的解释学过程的结构依赖于亚里士多德对“实践智慧”的分析[62],这里的实践智慧对应的是非科学的理解,这和他要在艺术领域和精神科学领域倡导非科学的真理观、反对科学主义、工具主义的主宰分不开;然而《真理与方法》直接讲“善”本身却很少(只是在该书最后一节提到一点[8](642-654))。至于到了第二部重要著作,“善”的理念本身成了贯穿始终的“主角”,并且深入揭示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善”的理念的内在联系(包括苏格拉底),将其呈现为一种影响史和效果史,它通向西方传统形而上学(这与海德格尔显然是不同的),其思想所达到的高度和境界,在某种意义上超过了《真理与方法》,虽然它的篇幅比后者少得多(而且主要是通过解释别人的思想来暗示自己的观点),可以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善的理念》是对《真理与方法》的形而上学之维,尤其是最具这色彩的最后一节“解释学的普遍性观点”的意义的“打开”。总之,这两本书之间经历了从“实践智慧”的重心向“善”之理念的重心转移,这种“转移”是一种升华,同时也表明二者的不可分性。
通过第二部重要著作对“善”的理念的探讨,伽达默尔将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总之,“phronese”和“sophia”统一起来了(实践智慧关注具体的善,而理论智慧关注普遍的善),而不像在《真理与方法》中是断开的(这也是笔者过去在未深入钻研他的第二部重要著作之前读其第一部重要著作时经常感到的困惑与不满意的地方[63]),它显然是一个重要的补充。作为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的核心——伦理学,不是一般的道德科学,它融存在论、目的论为一体,所以它是“哲学伦理学”,正如他的解释学不是一般的解释学,而是“哲学解释学”一样,这里的“哲学”包含存在论。这方面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康德具有某种一致性和典范性。而伽达默尔晚年要自觉地沿着这个方向推进一种和哲学解释学密切相关的哲学伦理学。
人们或许会问,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哪一个更伟大?应当说,都伟大,但如果一定要在两人之间做一个选择的话,我们不能不说,柏拉图更伟大,否则怀特海不会讲,整个西方哲学传统无非是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23]。对西方哲学开端的理解要从柏拉图开始,而不能
---------------------
[62]参见伽达默尔《诠释学II: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第27页;另参见何卫平《理解之理解的向度——西方哲学解释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42页。
[63]美国列奥·施特劳斯学派的成员也曾向伽达默尔提出过类似的问题(参见“访谈:伽达默尔论施特劳斯”,田立年译,载施特劳斯《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施特劳斯通信集》,朱雁冰、何鸿澡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499页)。
16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因为弄不好会容易理解偏。相对而言,柏拉图的思想更带综合性,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更带专题化,而且在伽达默尔眼里,不仅亚里士多德仍然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而且是第一个柏拉图主义者,连他本人也不例外,也仍然以其独有的方式充当柏拉图的“注脚”,并自称终生是柏拉图的学生[22](619)。他后来甚至认为,对柏拉图的研究才是他更具原创性的成果[64]。
与之相关,晚年的伽达默尔并未逃避形而上学,而是坦然面对,这和海德格尔曾经的追求有偏离,因为彼时的他认为,柏拉图主义等于传统的形而上学,是应当被克服的对象,但晚年的海德格尔思想有变化,认识到形而上学类似人的影子一样无法跳出,因此,他不再将对形而上学的“克服”理解为简单的抛弃,而是“经受”意义上的“痊愈”,伽达默尔注意到并强调了这一点[65],所以在《科学时代的理性》中,伽达默尔直接引用黑格尔的一句名言:一个民族若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神庙没有主神一样 [66]。在《真理与方法》最后一节“解释学的普遍性观点”中,他也承认,“随着我们的解释学探究所采取的存在论转向,我们就接近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概念”,“这就是美的概念”[8](642)。紧接着要发挥的就是柏拉图《斐莱布篇》中的观点:从真善美的统一中去理解“善”(这也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中期的对话《会饮篇》)。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善的理念》,伽达默尔更自觉地实现了一种向形而上学的回归,它集中体现为真善美的一致,它也可视为是对《真理与方法》最后一节思想的进一步延伸[8](647-651),这里暗示出伽达默尔第一部重要著作和第二部重要著作联结的一个枢纽,可见,伽达默尔在海德格尔之后致力于从解释学上去恢复形而上学的崇高地位,并以独有的方式将自己纳入到并隶属于这个传统[67]。海德格尔“转向”后,用“思想”取代“哲学”,而伽达默尔将自己的解释学仍命名为“哲学解释学”,始终强调自己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68],隐含对形而上学有保留之意,对于他来讲,解释学始终有一个形而上学维度,这显示出他与海德格尔的重要差别(哈贝马斯后来明确地指出了伽达默尔与海德格尔的这一差别[69])。如此看来,柏拉图的《斐莱布篇》对伽达默尔的三部著作都有深刻的影响,只不过在第一部和第三部著作中是显性的,在第二部著作中是隐形的(集中体现在该书最后一节“解释学的普遍性观点”中)。
与伽达默尔早、中期相比,我们可以看到,晚年的伽达默尔已从海德格尔巨大的“阴影中走出来了,真正建立起了他自己的哲学解释学,这种哲学解释学与哲学伦理学合二为一。而海德格尔本人的兴趣主要在存在论,认为存在论优先于实践哲学,因此,他并不怎么关心伦理学,有人甚至认为在他那里并不存在伦理学[70],列维纳斯第一个指出了海德格尔思想中
------------------------
[64]参见让·格朗丹《伽达默尔传》,黄旺、胡成恩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0年,第411页。
[65]参见伽达默尔《伽达默尔论黑格尔》,张志伟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第136-137页。
[66] 参见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46页;另参见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页。
[67]参见让·格朗丹《伽达默尔传》,黄旺、胡成恩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0年,第450-451页。
[68]参见“访谈:伽达默尔论施特劳斯”,载施特劳斯等《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朱雁冰等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497页。
[69]参见Jurgen Habermas, “After Historicism, Is Metaphysics Still Possible?”,in Gadamer’s Repercussions,Reconsidering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ed. by Bruce Krajewski,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2004, p.16,19.
[70]参见弗朗科·伏尔皮《以谁之名?——海德格尔与实践哲学》,刘明峰译,载《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25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第293页、泰布尔·德·布尔《胡塞尔思想的发展》,李河译,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6页、韩潮《海德格尔与伦理学问题》,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8页、10页、16页、21-22页;另参见·格朗丹《伽达默尔传》,黄旺、胡成恩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0年,第143页。当然,在海德格尔那里到底有没有伦理学学界一直是有争论的。“转向”前的《存在与时间》中虽然用了许多富有伦理意味的术语和表述,但他强调不带任何价值判断,仅仅是用于对此在“在世”的生存论结构的现象学描述,因此就其本人来说,很难谈得上是伦理学。“转向”后的海德格尔反对将柏拉图“理念的理念”,即“最高理念”译成“善”的理念,认为这是有失本义的误导,“善”的真正本义要理解成“适宜”,而不能理解成“道德上的善”,不能将其与一种伦理上的“价值”相联系(参见海德格尔《柏拉图的真理学说》,载《路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61-262页)。这似乎是要淡化“善”的伦理学意味,虽然海德格尔在《论人道主义的信》中提到过一种“源始伦理学”(参见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420页),这种“源始伦理学”是存在论意义上的,而非“基础存在论”意义上的(因为这个阶段他自己已放弃了“基础存在论”这个术语),但语焉不详。联系海德格尔在别处谈到“天地人神,四元圆舞”,其实讲的就是它们之间的“适宜”的关系,这种“适宜”似指向他所谓的“源始伦理学”,只是这种伦理学不是基于人的或人道主义的,但又不排斥人,而是强调它们之间的关系的“适宜”,它影响到当代的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不过,就海德格尔思想的整体来看,他是不太重视伦理学的,至少在论述上很薄弱,这与伽达默尔解释学十分突出这个领域形成鲜明的对比。
17
的伦理学的缺位[71],他的友人并深受其影响的保罗·利科也这样看,在谈到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时,他说,“我认为海德格尔的哲学以存在问题、本体论问题为重点,他的哲学完全没有道德和政治的选择标准。这是一种不能产生伦理学的本体论。因此,它没有内部防线”[72]。而这恰恰也是伽达默尔与海德格尔不同的地方。另外,海德格尔比较轻视辩证法,这也是伽达默尔与之不同的地方。可以说,伽达默尔晚年这部重要著作是其一生思想的总结与升华,真正标志着他彻底实现了存在哲学与实践哲学的统一、哲学解释学与哲学伦理学的统一、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并且更彻底地说明了“解释学就是实践哲学”这一根本命题,它表明解释学最终是导向“善”的,或者说,是追求善的解释学。至此,在他那里,实践哲学汇入第一哲学,甚至就是第一哲学(形而上学),与列维纳斯所说的“伦理学是第一哲学”异曲同工、交相辉映,这方面,他们都同海德格尔拉开了距离,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伽达默尔的思想暗示出,这种形而上学,不同于海德格尔所概括的“存在-神-逻辑学”,而是“逻各斯-努斯-伦理学”(logos-nous-etho)[73],但其意义不限于我们一般理解的伦理学或道德哲学,而是具有普遍的存在论意义,它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关联的梳理中得出,属于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开端和发展的正宗。伽达默尔晚年似乎要将他的哲学解释学对接到这种传统中去,并以此为奠基,真正确立起解释学的普遍性,从而与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划清界限。它能构成一种信仰、一种追求,一种人生的定力。
在生命之火行将熄灭之前,伽达默尔还在不断地说,“人类不能没有希望的活着”,这是他一生所追求的“唯一论题”、“唯一学说”[74]。这里的“希望”是和对“善”的坚定信念与追求分不开的(它让我们联想到了胡塞尔晚年对“理性”抱着坚定的信念和矢志不渝的追求),解释学不可能偏离这一维,而是始终包含这一维的,离开善的追求,解释学就会迷失方向。这种善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抽象的指它的第一哲学之维,具体的指它的实践哲学之维,二者是统一的,这就是柏拉图晚期的《斐莱布篇》中的“善”所暗示的。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不是对立的,而是相通的,这正是伽达默尔第二部重要著作的要旨所在,他也正是从这一层面看待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善”的理念批判的意义。
最后,笔者想引用伽达默尔的学生奥托·珀格勒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
所有人都从中期伽达默尔而来,都从《真理与方法》而来。但只要我们还没有接受他的晚期工作,我们就不能说,我们已经对伽达默尔有了深入的了解[75]。
------------------------------
[71]参见Jean Grondin, Sources of Hermeneutic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Albany, 1995, p.47.
[72]《利科访谈录》,张伯霖译,载《哲学译丛》,2001年,第1期,第60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另参见
[73]参见胡传顺《伽达默尔伦理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28页。
[74]参见让·格朗丹《伽达默尔传》,黄旺、胡成恩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0年,第458页。
[75]奥托·珀格勒:《黑格尔、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马飞译,载http://r-u-k.cn/wenku/yu006.html。在这一点上。由此看来,让·格朗丹这方面是有欠缺的,他所写的关于伽达默尔解释学的书(包括那部著名的《伽达默尔传》)对伽达默尔晚年愈来愈突出的“实践哲学”以及他的“第二部经典”都关注得很不够,就说明了这一点。
18
参考文献:
[1] Alasdair MacIntyre, “On Not Having the Last Word: Thoughts on Our Debts to Gadamer”, in Gadamer’s Century: Essays in Honor of Hans-Georg Gadamer, edited by Jeff Malpas, etc., The MIT Press, 2002, p.157.
[2] Gadamer, Idea of the Good in Platonic-Aristotelian Philosoph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viii.
[3] 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M]. 贺麟,王太庆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70,272。
[4] 维尔纳·耶格尔. 亚里士多德:发展史纲要[M]. 朱清华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5] 伽达默尔. 伽达默尔论柏拉图[M]. 余纪元译.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212.
[6] 君特·费格尔. 苏格拉底[M]. 杨光,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4.
[7] Gadamer, Platos dialektische Ethik, in Gesammelte Werke 5, Mohr Siebeck, 1985: 66-70.
[8] 伽达默尔. 诠释学I:真理与方法[M]. 洪汉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616.
[9] Gadamer, Plato’s Dialectical Ethics. Part I,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ix, p.1.
[10] Donald Davidson,“ Gadamer and Plato’s Philebus”, in The Philosophy of Hans-Georg Gadamer, edited by Lewis Edwin Hahn, Open Court, 1997, p.429.
[11] 海德格尔.柏拉图的《智者》[M]. 熊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8,868.
[12] Jean Grondin, Gadamer, a Biograph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25.
[13] 施莱尔马赫. 论柏拉图对话[M]. 黄瑞成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56.
[14] 汪子嵩等. 希腊哲学史:卷1[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18-323.
[15]
[16] 汪子嵩等. 希腊哲学史:卷2[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087.
[17] 伽达默尔. 论一门哲学伦理学的可能性[J],邓安庆译,《世界哲学》2007年第3期.
[18]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M]. 苗力田,主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241.
[19]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M]. 邓安庆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49.
[20] 马克斯·舍勒. 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伦理学[M]. 倪梁康,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7。
[21] 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奠基[M]. 杨云飞译、邓晓芒,校.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5.
[22] 伽达默尔. 诠释学II:真理与方法[M]. 洪汉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7,614.
[23] 怀特海《过程与实在》,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63页。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