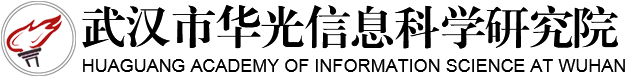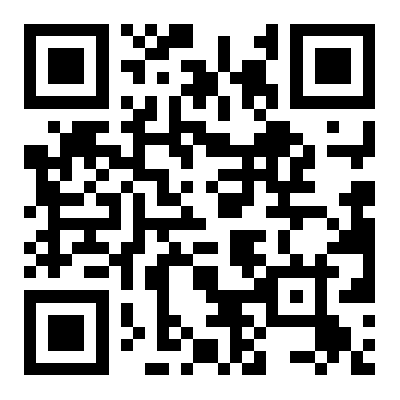网站首页 >> 2025 SIS 展示 >> 李宗荣,李凌斌:评《李宗荣与钟义信信息科
2025 SIS 展示
李宗荣,李凌斌:评《李宗荣与钟义信信息科学思想比较》
评《李宗荣与钟义信信息科学思想比较》
李宗荣,李凌斌
武汉市华光信息科学研究院
摘 要:鲁晨光在科学网博客上说:ChatGPTGPT根据我的提示写了这篇文章,即《李宗荣与钟义信信息科学思想比较》(简称《比较》)。我们读了这篇文章,沿着鲁晨光的表述思考发现:
(1)《比较》所说的李宗荣与钟义信信息科学思想的差异(简称李钟差异),不是个别观念和命题上的一般性“差异”,而是根本性的差异,是概念、原理与方法的差异,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差异;李宗荣主张“物质-信息”二元论的世界观方法论,钟义信主张“物质一元论”的世界观方法论。
(2)《比较》所说的李宗荣与钟义信信息科学思想的路径(简称李钟路径),不是方向相同的路径,而是方向相反的路径。李宗荣学习数理逻辑和程序设计,直接抵达信息本质及其运动的规律。而钟义信学习无线电通信与广播以及香农信息论,追随香农通信的数学理论,将其贯彻到一切非通信的信息过程,建立广义信息论,实际上是冒牌的假信息科学。
(3)《比较》所说的李宗荣与钟义信信息科学思想的互补(简称李钟互补),是“正1”和“负1”的互补。李宗荣的信息科学,克服钟义信自然科学范式对于信息科学研究的误导,记为“正1”。钟义信在信息科学中坚持自然科学范式,记为“负1”。这样,“李钟互补”的过程,导致中国信息科学在一条弯路(0→-1→0→+1)上走了50(1975-2025)年!
关键字:ChatGPT,鲁晨光,李宗荣,钟义信,信息科学,思想比较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李宗荣,男,湖北荆门人;1947年1月出生;武汉市华光信息科学研究院院长,研究员。196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获得理学博士与哲学博士学位;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研究领域:信息科学、信息哲学。代表作品:论文,《柏拉图理念论的日喻和线喻中的“殊相”与“共相”--------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论”以及当代理论信息科学的“范畴论”》;著作,李宗荣、田爱景:《社会信息学导论》,人民出版社,2010年。
1、鲁晨光提示ChatGPT写出《比较》的“摘要”与“结论”
《李宗荣与钟义信信息科学思想比较》(简称《比较》)[1] 的“摘要”是:随着信息被确立为继物质和能量之后的第三基本范畴,信息科学逐渐成为21世纪学术体系中最具前景的跨学科前沿。中国学界中,李宗荣与钟义信是两位代表性学者。前者在其博士论文《信息科学:概念、原理与方法》中提出“理论信息学”,强调信息的非物质属性和方法论转向;后者则通过“信息本体论”与“四元论框架”力图为信息科学建立哲学基础与整体体系。本文从学科定位、信息定义、学科体系、哲学立场、应用取向等方面比较两者的思想,并特别讨论了二人在“信息量化”问题上的分歧。研究表明:李宗荣强调信息科学应超越香农—Weaver范式,注重含义与价值;钟义信则强调量化扩展和体系化,注重形式化与学科地位。二者路径虽异,但具有互补性,为中国信息科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比较》的“结论”是:李宗荣与钟义信代表了中国信息科学的两种不同探索路径:前者以“理论信息学”为核心,强调非物质性与跨学科方法;后者以“信息本体论”为核心,强调量化扩展与体系化。二者的分歧,尤其在量化问题上的对立,揭示了信息科学未来发展中的关键张力。但两者亦互补:李的应用导向与钟的哲学导向结合,有望推动信息科学实现既有理论根基,又有应用实践的全面发展。
2、李宗荣与钟义信的信息定义的比较
2.1 钟义信的《信息科学原理》中,没有给出“信息”的“定义”。[2]
所谓给信息下定义,就是用简洁的语言规定信息的内涵和外延。钟义信的《信息科学原理》的1-5版,都没有给信息下定义。
(1)钟义信提出和建立所谓的“全信息”概念和理论,他涉嫌抄袭与剽窃Veaver的论述这里不细说,我们仅仅讨论他的公式:全信息=语法+语义+语用。这就像人们说:全苹果=果皮+果肉+果核。如果我们进一步忽略钟义信望文生义地误解“语义学”中的“语用”为“语言的用途”,将“语用”换为“效用”;那么,钟义信的公式仅仅是在解释一个“全信息”的构成成分,即“语法”、“语义”和“效用”,他并没有给“信息”本身下定义。
(2)钟义信定义了“本体论信息”和“认识论信息”,但是这不等于给“信息”本身下定义。比如,我们给“苹果”和“香蕉”下定义,并不等于给“水果”下定义。“信息”是“本体论信息”和“认识论信息”的“上位概念”。给“下位概念”下定义,与给它们的上位概念下定义,根本就是不同的两件事情。
2.2 钟义信给“本体论信息”下的定义是“物质一元论”的,因为他说,信息是“事物运动状态及其方式的普遍表现”。
这个信息的定义,仅仅适合于理解“物质运动状态及其方式的普遍表现”;而人类“文化”,“论文”和“著作”的“信息”,看不见它们自身的“运动状态及其方式”,也不知道其“普遍表现”。比如,钟义信根本不能告诉我们:他的《信息科学原理》具有什么样的“运动状态”、“运动方式”,更不能描述它们的“普遍表现”。
2.3 李宗荣的信息定义是“物质-信息”二元论的,信息是“信号与符号所载的含义”,信息的本质是非物质的“意义”。[3]
宇宙万物都由“物质”和“信息”组成,物质是“载体”,为我们的“肉眼所见”;信息是载体的“含义”,为我们的“心智所见”。从幼儿园小朋友的《看图识字》,到小中大学的统编教材,都在教育我们,如何用“心智”去“观看”文章和著作的“含义”。信息是非物质的存在。在钟义信的信息定义中,完全没有揭示出“信息”的本质特征和属性。信息的“载体”,要么是“信号”,要么是“符号”;而符号是信号的信号。还有比这更加简洁、直白的定义吗?
3、李宗荣与钟义信信息科学体系的比较
《比较》说:李宗荣信息科学知识体系的结构是:“1+4+3”:1门(理论信息学)+ 4门(通信、控制、计算机、机器人)+ 3门(自然、社会、人文信息学),呈纵向层级结构。情况属实。
但是,《比较》说,钟义信信息科学知识体系是“四元论”,即:“符号科学”+“系统科学”+“控制科学”+“智能科学”,它们四者并列地支撑信息科学体系。这是100%的瞎扯。
李宗荣自1994年以来,全力推进信息科学的建立,试图解决国内外“只有信息技术,没有信息科学”的局面。那些主张“没有信息科学”的学者说,所谓的“信息科学”的核心和关键是“计算机科学”,而计算机科学在实质上是数理逻辑和微电子学的“应用学科”,“生物信息学”是它们的应用的“再应用”而已。如果数学和物理学把自己的东西拿走,那么计算机科学还剩下什么,它有其他学科拿不走的东西吗?
在钟义信的“四元论”的“信息科学”中,符号科学、系统科学、控制科学、智能科学都是自成一家的“科学体系”;固然它们与信息科学有某种联系,其研究对象可能有某种交叉,但是,因此钟义信就“收编”这四门科学作为信息科学的四个组成部分,如果人家要“拿走”,那么钟义信的“信息科学”自己还有什么能够留下来的呢?显然,所谓钟义信信息科学体系的“四元论”,是100%的瞎扯!
4、李宗荣与钟义信信息科学实际应用的比较
《比较》说:李宗荣与钟义信信息科学的应用取向差异是:
(1)李宗荣:重点在信息心理学与人工智能,提出“人是信息复制与生成系统”,分析智慧的涌现机制。这基本上符合实际,因为建立信息科学的主要目的是引领和指导“信息技术”。目前的信息技术有两个大的领域,即“心理援助”和“人工智能”。“信息心理学”是心理援助的基础理论,是理论信息学在“理论心理学”中的应用。在严格的意义上,迄今为止,智能科学并没有建立起来。
(2)钟义信:重点在信息哲学与系统科学,推动信息哲学的发展,强调学科话语权。这又是瞎说。钟义信的“信息科学”本身,是“物质一元论”的,它用来支撑的“信息哲学”必然不是“物质-信息”二元论的,显然只能是片面性的信息哲学。至于“系统科学”,根本不需要钟义信的信息科学的“应用”,人家本来就是“自然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孕育的结果,不需要按照钟义信的说法,再来一次“自然科学范式”的“应用”。
5、李宗荣与钟义信信息科学基本假设与逻辑前提的比较
《比较》在“哲学立场”差异中说:
(1)李宗荣:主张“物质—信息二元论”,世界由物质和信息双重构成;强调方法论转向,以信息视角重建心理学和社会科学。这基本属实。
(2)钟义信提出“世界三元论”,物质、能量和信息共同构成世界本体;强调信息的普遍性和本源性。这是在为钟义信挖坑,给他塞进一个“抄袭”与“剽窃”的嫌疑。因为,维纳在1948年就说,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从此,产生了宇宙构成“三要素”(物质、能量、信息)的说法。怎么又变成是钟义信“提出”的呢?
把“世界三元论”安插在钟义信的头上,是错误的。但是,钟义信不能打破“三元论”的束缚,是他的所谓人工智能理论的根本性的“短板”。如果世界上根本没有“智能”这个东西,何来“人工智能”?所以,人工智能理论的基本假设和逻辑前提是:超越维纳的“三要素”,建立“四要素”理论,即“物质、物理学能量;信息、信息学能量”。信息学能量简称“信息能”,宇宙万物都有信息能;人类的信息能是“智能”,机器的信息能是“人工智能”。否则,人工智能的理论基础就不能自圆其说。可惜,目前的智能科学的许多研究者,很难从“三元论”跃升到“四元论”。
《比较》还说:“李偏向方法论实用主义,钟偏向哲学本体论。”在实际上,钟义信根本不知道“哲学本体论”是什么;看看他的所谓“本体论信息”和“认识论信息”的定义,就能够知道他的哲学基本知识的欠缺。
《比较》在“关于量化的分歧”中说:李宗荣与钟义信“在量化问题上,分歧尤为明显:”
(1)钟义信:以 Weaver“三层次”为框架,主张将语法、语义、语用全面纳入信息科学,尝试量化语义与语用信息,保持形式化的科学性。
(2)李宗荣:批评其“过分依赖量化”,认为语义与语用涉及意义与价值,无法完全度量。若过度量化,会导致信息再次物质化,丧失非物质属性,难以解释心理与智慧现象。
《比较》总结道:钟偏“工程—量化”之路,李偏“哲学—方法论”之路。分歧体现出信息科学发展的两极张力:一极追求数学化统一,另一极追求意义与价值解释。
李宗荣的信息科学认为,可以数量化的是信息的物质载体,而不是信息本身;钟义信给出的信息“识别”、“认知”、“再生”、“思维”、“施效”、“组织”的数学公式全部无效,不可能被经验实证。
在物理、化学、生物的场景中,物质的研究对象都是可以被数量化的,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中确定它们在某个时刻的具体位置,更可以用数学公式(比如,H=G*T*T/2)表达物质运动(比如自由落体运动)的轨迹。任意给出一个时间值T,就可以计算出物质运动的空间坐标。那么,请问:按照钟义信关于“信息”的数学公式,给一个时间T,能够算出什么来?
在信息科学中,能够数量化的是信息的“载体”(即“载体信息”),而不是“信息”本身,即“纯粹信息”是不可以数量化的。比如,钟义信的《信息科学原理》的第1-5版,可以通过“数学公式”计算出来作者“思想”运行的“轨迹”吗?可以用数学公式描述从第1版向第5版运动的轨迹吗?所以,上述种种美丽的数学公式,没有一个是可以被“经验实证”的。提出一批非数学科班不能懂得的公式,描述信息现象,是“自欺欺人”。比如,我说:我的行为Y,是我的心态Xt的“函数”,记为“Y = f(Xt)”。请问,如果没有我的“心态”和“行为”的公认标准(像重量“公斤”和长度“米”那样)在任何时间(t)都可以准确测量的“数量化”,这个“Y = f(Xt)”中的“f”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我们给予一个t的数值,代入公式,可以计算出什么结果来?这种“数学公式”的作用,除了自欺欺人,还有什么用处?
香农所说的通信工程,不考虑所传递“消息”的“含义”,因此可以视为纯粹的“物理过程”。对于通信工程,这样处理是必要的,应当的,可能的。电报、电话公司,微信与QQ系统传递“消息”当然不能顾及“含义”,否则就要根据“消息”是积极地还是消极的,收取不同的费用。真正对于消息的含义感到兴趣的是政府安全部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全部学科,没有哪一门学科不顾及传播中消息的“含义”。但是,这种“含义”可以按照物理、化学、生物学的标准来度量吗?可以给出每个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信息过程以数学公式的准确表达吗?
所以,对于信息进行“数量化”与“公式化”研究,追求所谓的“数学化统一”,而且夸大成为“体现出信息科学发展的两极张力:一极追求数学化统一,另一极追求意义与价值解释”,这本身只能是相关研究者的一种“自我安慰剂”,似乎可以在“自欺欺人”中得到成就感。哲学认识论关于“真理”标准是:融贯论、符合论、实用论。中世纪哲学家们研究一个针尖上可以站立多少个天使,他们写出大量的论文和著作。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层出不穷。还有人曾经声称,可以“用数学方式证明地球是平的”。如果某人的价值选择就是如此,他们自说自话、自得其乐,我们不必干涉,也没有任何义务和责任去改变他们。李宗荣的一个数学科版的朋友在某大学研究“数量经济学”,称它是“文科”中的“理科”。李宗荣当面质疑:既然你可以数量化、公式化了,那么请你算算,下一次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发生在笛卡尔坐标系的什么位置、什么时候?那个朋友只能老实交待:吓唬那些不懂数学、害怕数学的杂志编辑而已;你搞几个公式上去,他们就晕了,分不清好坏与是非。呵呵,原来如此!
7、李宗荣与钟义信信息科学原始创新工作的比较
《比较》在“引言”中说:在中国学界,李宗荣与钟义信分别提出了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构想。(1)李宗荣主张建立“理论信息学”,作为信息科学体系的元科学,强调信息的非物质性和方法论更新;(2)钟义信则提出“信息本体论”与“四元论”。
李宗荣的“理论信息学”是在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勇传导师的指导和帮助下,他有一个四人的指导团队在一起工作。论文的开题与答辩,都有3-4位院士参与。 所以,李宗荣的成果不仅仅是李宗荣一个人的。因为李宗荣在开题报告中主张,明确自然科学的适用范围,批评自然科学方法僭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错误,必须建立与发展信息科学独有的“范式”,在开题时遇到几位物理学家的激烈反对。他们说,李宗荣不仅为自己“开题”而且为当代的人文社会科学家开题了;不仅李宗荣做不完,连李宗荣的儿子、孙子也做不完。但是,最后张院士批准了李宗荣的《开题报告》,而且2年半就做完了,通过了学位论文的答辩。所以,一批受到“物理学羡慕症”和“数量化情节”严重影响的学者,排斥和拒绝李宗荣的信息科学范式,并不是非常的“不正常”。真理从来都是在同谬误的竞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真理一开始总是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一个人的手中;这种“存在”是有它的“合理性”的。
一个人所受到的“教育”,所作过的“工作”,必然对他造成“路径依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如此。马克思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指那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物质的和精神的“遗产”。钟义信受教育的地点和环境,培养他严守香农的世界观方法论,而且在研究中,他不遵守《著作权法》关于各类研究人员不得“抄袭”和“剽窃”的规定,不遵守《科学技术进步法》关于“不得在科学技术活动中弄虚作假”的规定;钟义信在实际上“引用”了前人和同时代学者的成果,但是不说明他人成果的出处;钟义信稍加改动,就成为他自己的“创新”,就宣布他“提出和建立”了“全信息”理论,主张他研究的“广义信息论”就是“信息科学”。
而且,钟义信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如今21世纪20年代中期,前后近50年,半个世纪中坚持他的所谓“发明”与“创新”。并且,为了巩固他的主导和领导地位,采用“非学术”的手段和方式,压制信息科学的发展,打击他的“全信息”理论的竞争者,以达到他的目的。这种现象,并不是不能理解,在《科学蒙难集》[4] 上的故事太多了。俗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钟义信的“不义”做得太多了,造成的对立面也太多了;而且他坚持的时间太长了,半个世纪,他压制的对象必然会逐步地站立起来、组织起来,形成“合力”。最后,他自己受到“真、善、美”的批判和清算,其报应也就顺理成章了。
8、参考文献
[1] 鲁晨光. 李宗荣与钟义信信息科学思想比较------ChatGPT, 2025-8-25 07:37
|个人分类:信息的数学和哲学|系统分类:观点评述.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056&do=blog&id=1498967
[2] 钟义信. 信息科学原理(第5版). 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13年.
[3] 李宗荣:《理论信息学:概念、原理与方法》,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
[4] 解恩泽. 科学蒙难集. 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