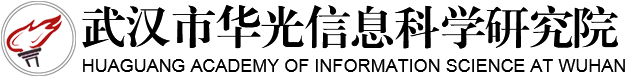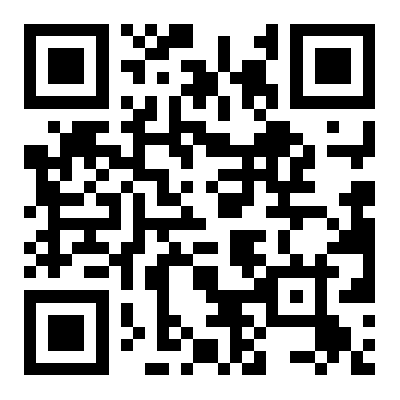网站首页 >> 2025 SIS 展示 >> 吴垠翰:卡普罗信息哲学的思想内核及其对统
2025 SIS 展示
吴垠翰:卡普罗信息哲学的思想内核及其对统一信息理论的启示
卡普罗信息哲学的思想内核及其对统一信息理论的启示
吴垠翰
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中国北京
摘 要: 德国信息哲学家拉斐尔·卡普罗(Rafael Capurro)提出的“三难困境”(Trilemma)深刻揭示了构建统一信息理论所面临的根本性挑战,即信息的定义无法同时满足普遍性、精确性与实质性这三个维度。本文旨在深入剖析卡普罗信息哲学的核心思想。首先,将阐释“三难困境”的哲学根源及其为何成为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其本质在于信息现象跨越了物理、生物、社会等多个存在层次,任何单一视角的定义都会丢失其他层面的丰富性。其次,文章将探讨卡普罗如何受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现象学和解释学传统的影响,将信息理解为一种关系性存在和意义生成事件,而非一个静态实体,从而为克服“困境”提供了哲学框架。最后,本文认为,卡普罗的贡献不在于解决了困境,而在于将其从一个需要被消除的“障碍”转化为一个富有建设性的分析工具和反思起点。这启示我们放弃对绝对统一理论的追求,转而采纳一种基于多元视角互补和动态关系建构的信息科学观。
关键词: 卡普罗;三难困境;信息哲学;统一信息理论;德国哲学;信息概念
 个人简介
个人简介
吴垠翰,女,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在读。出生于2001年6月,本科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德语专业,现为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在读研究生。曾于《文化产业》发表区域国别研究相关领域论文《印度电影中歌舞元素的叙述功能探析》;参与国家社科重大基金项目“西方国家主要政党涉华传播话语体系研究”;参与撰写“欧洲主要媒体对‘一带一路’峰会报道的新关注点及应对建议” 咨政报告。
邮箱地址:2649089297@qq.com;联系方式:13120167106。
1.引言
我们正置身于一个前所未有的“信息时代”。从人工智能的崛起到大数据的泛滥,从社交媒体的全球互联到物联网的悄然渗透,信息科学技术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着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深刻地改变着我们认知世界、互动交往乃至存在的方式。然而,在这片技术繁荣的景象之下,一个基础性的哲学困局却始终如影随形:信息科学的实践蓬勃发展与其核心概念——“信息”(Information)之于哲学基础的模糊不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1,闫学杉】。尽管“信息”一词被各个学科广泛使用,但当我们试图追问其本质时,却陷入了一种令人尴尬的境地:计算机科学家、生物学家、传播学家和社会学家所谈论的“信息”,似乎是同一个词指向的完全不同的事物。这种概念的混乱与模糊,使得信息科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根基始终备受质疑。
在此背景下,构建一个能够统摄所有领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信息理论(Unified Theory of Information, UTI),便成为了许多信息科学家与哲学家的“圣杯”与梦想。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诸多学者投身于此项事业,试图弥合不同学科间的鸿沟,为“信息研究”提供一个坚实、统一的概念基石。然而,尽管努力众多,但所有尝试似乎都未能取得普遍共识,成功的曙光依然渺茫。这就引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为何构建统一信息理论如此之难?其背后究竟存在着怎样难以逾越的哲学障碍?
德国信息哲学家拉斐尔·卡普罗(Rafael Capurro)提出的“三难困境”(Trilemma),为我们分析这一根本性难题提供了一把关键的钥匙。他指出,任何对“信息”的定义都无法同时满足三个理想条件:普遍性(universal applicability)、精确性(precision)与实质性(substantiality)【2,Capurro】。追求普遍性往往会牺牲精确性,确保精确性可能无法涵盖所有信息现象,而一个高度抽象的形式化定义即便兼具了一定的普遍性和精确性,又可能因脱离具体语境而失去解释力的实质性。这一困境深刻揭示了信息概念的内在张力,它并非一个可以轻易解决的技术性难题,而是揭示了信息现象本身固有的、多元的、跨层次的本体论特征。因此,对卡普罗“三难困境”的深入剖析,是理解统一信息理论为何屡屡受挫,并重新思考信息科学之哲学起点的必经之路。
2.统一信息理论为何不可能?
“三难困境”的三个维度构成了一个近乎完美的“不可能三角”。其中普遍性要求信息概念能够跨越学科边界,适用于从物理、生物到社会、人文的所有领域;精确性要求概念必须清晰、明确、可形式化,能被数学模型所描述;实质性则要求概念必须能够捕捉到信息现象独特的、本质的内涵,尤其是其与“意义”和“价值”相关的层面。
在具体实践中,这三个维度呈现出难以调和的内在冲突:香农信息论提供了精确且强大的框架,将信息定义为“不确定性的减少”,用比特作为量化单位【3,Shannon】,这个概念在通信工程领域极具实质性,但其普遍性却严重不足,因为它排除了信息的语义和语用维度。日常语义信息将“信息”理解为有意义的消息或知识,这个概念具有极强的普遍性,我们可以谈论“新闻信息”、“基因信息”、“市场信息”而毫无违和感,也充满了实质性,但其致命缺陷在于精确性的缺失。“意义”是模糊、主观且高度依赖语境的,难以被量化或形式化。形式化定义路径试图通过高度抽象的定义来追求普遍性和精确性,例如将信息定义为“差异的差异”或“数据和意义”【4,Bateson】。这类定义试图囊括所有层次的信息现象,并且听起来足够精确,但它们往往牺牲了实质性,沦为一种哲学上的“正确废话”,对于解决具体的科学问题难以提供真正的指导。
“三难困境”表面上看是一个定义的选择难题,但其深层根源在于信息现象本身在存在论上的多元性。信息并非一种单一的存在物,而是跨越了多个截然不同的实在层次的现象,它同时是物理符号、生物信号和人类意义。这些不同层次的现象遵循不同的规律,物理层次遵循因果律,生物层次遵循生命法则,而社会文化层次则遵循规范和价值律则。传统“物质一元论”的哲学预设在此显得力不从心,该预设认为所有现象最终都可以还原为物质及其物理属性,在这种观念下,构建UTI的路径就表现为将人类层面的“意义”信息还原为生物层面的“信号”信息,再进一步还原为物理层面的“符号”信息,最终用物理学或数学的语言加以统一描述。然而,这种还原的代价是巨大的,它恰恰必然导致“实质性”的丧失。当我们把贝多芬的交响曲还原为声波频谱图,再还原为二进制数据流时,我们得到了精确的、可普遍应用的物理描述,但却完全失去了其作为音乐艺术震撼人心的本质。信息的价值恰恰在于其在不同层次上涌现出的、不可还原的新属性。
因此,“三难困境”并非一个等待被聪明方案解决的技术性难题,而是信息存在方式之多元性和复杂性的必然体现,它从根本上揭示了在传统追求单一、还原论的实在论框架下,构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信息理论是不可能的。卡普罗的困境之所以难,正是因为它迫使我们正视一个事实,即信息只能是一个“共同类似”概念,其统一性可能并非源于一个共同的本质,而是源于不同现象之间复杂的网络关系。承认这一点,不是失败的宣告,而是迈向更成熟、更负责任的信息科学研究的第一步。
3.从定义信息到理解信息化
面对三难困境所揭示的理论僵局,卡普罗的卓越贡献在于开辟了一条彻底的超越之路。这条路径的哲学根基深植于马丁·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与解释学传统,实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向:从执着于追问静态的信息是什么,转向动态地探究信息如何显现,即关注信息化的过程本身。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存在者与存在进行了关键区分,批判传统形而上学沉迷于追问实体而遗忘了存在本身的意义开显过程。卡普罗深刻继承了这一思想,指出信息哲学的核心谬误在于将信息当作一个现成的、等待被定义的存在者,而忽视了信息首先是此在在世存在的一种根本方式,是一种去蔽的事件。
基于此,卡普罗提出了一个奠基性的命题:信息即是告知,这里的告知并非简单的消息传递,而是在存在论意义上,世界对此在的展开与此在对世界的理解相互交织的进程。信息因而被理解为一种关系性的事件和意义生成的过程,它并非预先存在于主体或客体的任何一方,而是存在于主体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之中,在具体的、历史性的语境中得以涌现【5,Lévy】。
为了系统阐释信息如何显现,卡普罗发展出了其思想的核心框架——信息的三重存在方式。这绝非对信息的三种并列定义或分类,而是对同一信息现象在不同关系语境中显现模式的深刻描述,三者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第一重是作为实在的信息,关注信息的客观性及其物理载体层面,例如构成数字图像的比特序列或DNA的分子结构。这一维度对应于香农信息论所处理的领域,确保了信息的可计算性与可操作性。然而,若仅停留于此,信息就沦为无意义的差异。第二重是作为意识的信息,涉及信息被主体感知、解释和理解的意义层面。此时,物理符号必须被一个意识主体接纳并赋予意义,才能成为信息,例如用户从手机屏幕上识别出文字和图像的含义【6,肖珺、张驰】。这一维度凸显了信息的意向性,它总是为某人、为某一目的的信息。第三重是作为交流的信息,关乎信息在主体间传递、共享并藉此建构社会现实的层面。信息在此成为一种社会行为,其意义通过交往得以协商、确认和修正【7,Castells】。这三重方式构成了一个连贯的范式:任何完整的信息现象都同时蕴含这三个维度,它们相互依存,不可还原。
基于上述存在论框架,卡普罗对三难困境的解决策略展现出其深刻的哲学智慧。他的策略并非要消除或克服这个困境,而是从根本上接纳它并将其转化为一个富有建设性的分析工具。他认识到,困境中所揭示的普遍性、精确性与实质性之间的张力,并非一个需要被抹平的缺陷,而恰恰是信息存在之多元性和层次性的真实反映。因此,三难困境本身不再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形而上学难题,而蜕变为一个极具价值的方法论原则【8,Haraway】。它可以被用作一个批判性的反思工具,用以诊断和评估任何一项信息理论研究或技术应用:它偏重于哪个维度?又忽略了哪些维度?其局限性何在?例如,一个纯粹工程取向的大数据分析项目可能极度偏向作为实在的信息维度,追求处理的精确性和效率,却严重忽视了数据背后的社会意义及其对不同群体的差异化影响,从而可能导致算法偏见。而一个纯粹人文取向的意义阐释可能充满了实质性,却在精确性和普遍应用上有所欠缺。
卡普罗的框架要求研究者必须保持方法论上的自觉,明确自身研究的视角和界限,承认自身进路的片面性,同时向其他维度的解释保持开放。这种从追求绝对统一到保持反思性张力的转变,正是卡普罗对信息科学最宝贵的贡献。他将信息哲学从一种致力于建构宏大体系的理论努力,转化为一种持续进行的、批判性的实践哲学,提醒我们在技术时代,既要以精确的工具去操作信息,更要以其全部的意义丰富性去理解和珍视信息,并在交往中对其负责。
4.信息哲学与信息科学的共生关系
信息科学是否真正存在?这一质疑源于以经典自然科学为范本的学科观念,即要求拥有统一范式、普适定律和明确界定的研究对象。若以此为标准,追求单一范式的信息科学确实面临存在性危机。然而,这种质疑本身可能建立在过时的学科观念之上。信息科学更适合被理解为一种“学科集群”,其统一性不在于共享一个精确的定义,而在于共同关注一个核心问题域——各类信息现象的产生、传播、处理和效用【9,闫学杉】。从计算机科学到生物信息学、从情报学到传播学,这些学科虽然方法各异但都围绕着信息这一核心现象展开研究。
在这一图景中,信息哲学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它不再试图为某个“不存在的”统一科学提供奠基性定义,而是为这个现实存在的、多元的学科群提供连贯的哲学说明和批判性的自我意识。信息哲学通过审视各学科的基本预设和方法论选择,帮助它们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和可能性。例如,当计算机科学家设计算法时,信息哲学可以提醒他们关注算法决策中的伦理意涵;当生物学家使用遗传信息概念时,信息哲学可以帮助他们反思这一概念的隐喻性质和本体论承诺。这种批判性的自我意识对于信息相关学科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与英美分析传统相比,卡普罗代表的德式信息哲学展现出独特的理论品格——关注信息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意义生成、强调信息的关系性和过程性。这一传统的优势在于其处理意义、历史和语境问题的能力,能够更好地把握信息的人文和社会维度。例如,在理解社交媒体上的信息传播时,卡普罗的框架不仅关注信息的传递效率,还注重信息如何在使用者之间生成共享意义,如何塑造社会关系,以及如何嵌入特定的文化历史语境【10,Lévy】。这两种传统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可以形成有益的互补。例如,在设计自动驾驶汽车的决策算法时,既需要形式化框架来确保算法的精确性和可靠性,也需要卡普罗式的现象学反思来关注算法决策的意义和伦理意涵。
信息哲学的未来发展或许不在于追求单一的理论范式,而在于保持这种批判性的对话张力,让不同传统在相互质疑和相互启发中共同深化我们对信息的理解。
5.走向反思性的信息科学观
卡普罗的信息哲学为构建当代信息科学观提供了重要启示,首要的启示是推动信息科学从“帝国模式”转向“共和国模式”。这意味着需要放弃构建统一理论帝国的梦想,转而接受一个由多种范式和方法共存的学科生态系统。在这个大一统的学科共和国中,计算机科学、传播学、生物信息学等不同学科可以平等对话,在各自保持方法论独特性的同时又围绕信息这一共同主题展开交流合作。
卡普罗的框架亦强调反思性实践的重要性。所有信息实践,包括算法设计、数据治理和人机交互,都需要自觉反思其背后的信息观【11,Castells】。例如,开发者应该考量其算法偏向三难困境中的哪个维度:是强调效率的精确性维度,还是关注用户体验的实质性维度,或是追求广泛适用的普遍性维度?这种反思应该进一步延伸到伦理层面,考察技术选择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12,Floridi】。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这种反思性实践可以帮助预防算法偏见、保护隐私和促进公平。
综上所述,卡普罗信息哲学的核心贡献在于以其深刻的批判性,将信息研究的焦点从“追求统一定义”引向“理解关系建构”。通过提出三难困境,他揭示了信息概念的内在张力和复杂性,打破了追求简单化统一理论的幻想。更重要的是,他通过现象学-解释学的进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信息的新方式:信息不是静态的实体,而是动态的关系性事件,是意义在具体语境中生成和流通的过程。三难困境的宝贵价值在于它作为一种永恒的提醒,防止信息研究陷入任何一种形式的简化论。无论是将信息还原为比特的物理简化论,还是将信息抽象为纯粹意义的意义简化论,都会失去信息现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个困境要求我们始终保持批判性的自觉,在研究和实践中注意不同维度之间的平衡和协调。
信息科学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其多元性和实践性。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研究信息现象,开发各种信息技术,解决各类信息问题,这种多元性不是弱点而是优势。信息哲学的任务就是守护这种多元性,为各学科提供哲学反思的工具,帮助它们认识到自身的预设和局限,促进它们之间的对话和合作。最终,信息哲学的目标是为信息时代提供深刻的人文关怀,确保技术的发展服务于人类的福祉和生态的可持续性。在这个意义上,卡普罗的信息哲学不仅是对信息本质的思考,更是对技术时代人类处境的深刻反思。
参考文献
【1】闫学杉. 信息科学:概念、体系与展望[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570-572.
【2】Capurro, R. (2009).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concept of information. tripleC, 7(2), 125-141.
【3】Shannon, C. E., & Weaver, W. (1949).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4】Bateson, G. (1972).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5】Lévy, P.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Mankind's Emerging World in Cyberspace. Basic Books, 1999.
【6】肖珺,张驰. 互惠性意义共通:朝向文明交流互鉴的数字化符号表意阐释. 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年度报告,2024.
【7】Castells, M.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Wiley-Blackwell, 2010.
【8】Haraway, D. 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In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Routledge, 1991.
【9】Floridi, L. 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